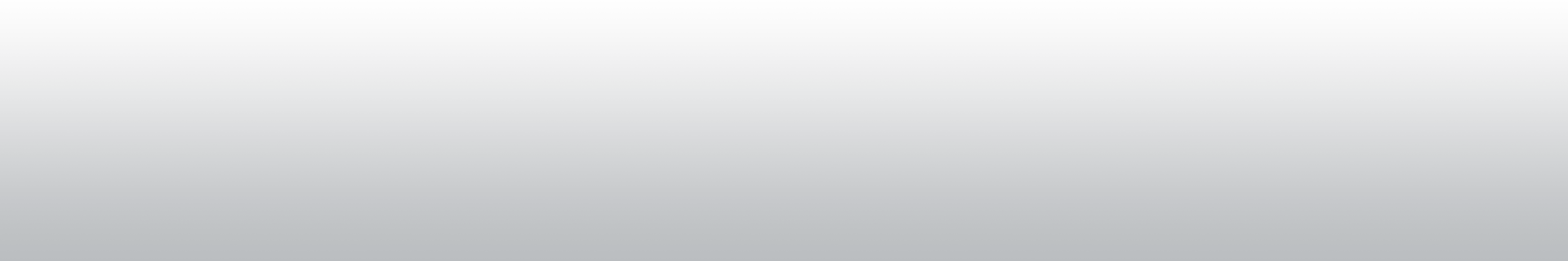人类自离开前肢直立行走始,直接影响其生活情趣飞升且传世更为多广并具极大研究价值的史料,并不是那些事后追记的文字典籍,也不是口头传唱的诗歌音乐,应属那些千古不朽的画作。因为后者更富有原始意象,也更广含现代人类探索祖先需要的直接信息。
从陆地到海岛,从森林到草原,那些用心涂抹在岩石上的飞鸟走兽,镌刻在洞窟石壁上的狩猎舞蹈;教堂庙宇庄严肃穆的彩绘,阁楼旧书箱里的珍贵遗作……这些一幅幅或令人面红耳赤、或惊心动魄、或肃然起敬、或为之颤栗的惊世遗作足以说明,绘画与欣赏,从来都不曾走出过人类的日常生活。

人类的幼年之所以发现手绘这一功能,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娱乐、记载、祭祀,并不看重“画作”的美学意义。到了新石器时代,图案美术便渐渐进入人类日常生活。比如陶绘,以及帛锦的花色,心目中神灵的形象,天上的太阳云朵,地上的山岳江河……于是,“画匠”这个职业便有了社会分工上的名分。进入农耕文明阶段,由于文字普遍用于思想交流,美学这个范畴的逐渐确立,才奠定了“美术”这个形而上的玩意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眼下,大多数人类社会已经到了后工业文明阶段,对于今天那些准备借助“美术”这张虎皮,用以贩卖自己思想的人来说,如果还停留在“娱乐”和“技法”层面上去思维,未免就有点唐突和猥亵。要想投身去做一个真正的画家,首先得具备脱胎换骨、出家礼佛般的超人毅力和坚强决心。这对于一介凡夫俗子,那不啻是一场噩梦,一生的苦旅。这也正是当代书画大家为何“寥寥霜雁两三声”的真实原因。
可是活在当下,眼热这个买卖的人却并不老少。偶尔参加一个小小的应酬饭局,这头刚刚坐定屁股还没来得及摸筷子,动辄就能收到几张冠以华人世界级的“书画协会主席”以及“中国画·第一人”之类名片。名片背后,少不得还印有一串“某大赛金质奖获得者”“某大作被某某名人堂入藏传世典籍”之类文字。再不济,也诌些地震饥荒后,此人曾捐出多少作品供义卖赈灾的善举云云……闹得你不由低头沉思:七十二行,难道成了卖画为强了么?要不然,眼下怎么一夜间冒出了这么多陌生的“水墨”人物呢?
如果让老牛说一句多有得罪的话,那些身处社会底层、整天钻背巷子化缘的假和尚假尼姑之类人等,在当下的神州大地可谓是随处可见且人数众多;可是,那些留着满脑袋长发、混迹于上流会所的一些自诩、自封、自吹、自擂的“书画大家”,会不会让人感觉比全国的假和尚还要多些呢?
诚然,在商品社会里,跻身为一名画家,就有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大把的银子。一幅好的画作,自然具有相应的商品价值。问题是,这个“好”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又让什么人来评判?而且,我们一些把持着这个行道话语权的衮衮诸公,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大有人在。更何况,我们身边的地铁橱窗和摩天大楼喷得随处皆见的“办证”电话,闹个货真价实的各类获奖证、鉴定证更不在话下呢。唉,这几句抢白,算是题外话也罢。
话又说回来,做为一个美术从业者,靠着脑袋瓜子里的小机灵在师傅处偷得一点混饭手段,关着门描几幅惟妙惟肖的小鱼小虾,绘一张古人存世的遗作,收得了四下里稀稀拉拉的喝彩,终于也换取了吃饭的衣钵,然而,切不要忘乎所以。说破天去,你充其量也还是个画匠。至于那些趁着身在官场、学场、人场有点职务特权,心血来潮之余便在宣纸上涂抹一番,再喊来几个无良说客去酒肆相互吹捧为之的“大作”,终于还唬得一些心照不宣的人掏了腰包拿去送礼,最终捞得个钵满盆满,你偷着数数腰包里的钱数完全可以。可是,你不要腰里别耗子,冒充打猎人。更不该大言不惭地号称什么“大家”,免得落得背地里被人指戳。

当然,在中国水墨这个宽阔的航道上,那些尊古效法、努力探索、登堂入室、功成名就的书画大家还是有的。只是不多。据老牛这个门外汉估算,在汉文化圈配得上“书画大家”此类名号的当代人物,大概不会超过七八个人。同样,能操笔评说这些大家画作的人数,大体与之相当。那些具有潜力,亦有可能接近跻身这个名单边缘的人子,屈指可数,至多不会超过百二十号人马。尽管他们苦读山水、虔心学画,并以自己生命的全部代价去认真体味这一瑰宝的古往今来,并把水墨已经操持得可谓随心所欲,工夫亦全在画内。有道是,只要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他们全然不会像那些投机者那么自信地四处招摇的。当然,他们也不需要、更没那些闲工夫去招摇。
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无论是操持书画还是从事文字书写这些个营生的人,没有将寻常的山山水水百看不厌的灵性和动辄发现其中微妙之处的法眼,凭着一点个人天资或后天的刻苦努力,一辈子都不可能在这两个行道上修炼到“家”的。
老牛也有几个画画写字的朋友,他们有的已经成家,有的还在路上。成家的也不算声名显赫,苦熬的依然默默无闻。可是,他们都具有天赋颖资、献身精神,甚或死后亦可能被人追念的潜力。因为,他们一个个都十分敬畏自己手中的笔墨。他们笔下的东西,让面读它的同类疲惫的灵魂时时就有了那种久违的喜怒哀乐的萌发,增添着他们继续好好活下去的勇气、激发起他们改天换地的豪迈冲动。这,就足够了。
年中,有上海朋友李晓虎先生为故乡的穷孩子求学救助一事,纠合了一支“黔西南之旅”。微信告知,天津画家尹沧海亦在邀请之列。一听这个名字,老牛倒是似曾相识,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何况,鄙人惦记着的朋友分时常见面和未曾谋面两大类,有些朋友至今还在天各一方,却时时觉得就在身边。于是,担心自己将此公和一个大和尚的名号搞混了,赶忙打开微博人圈搜索,哇呀,原来他正是南开大学那个博士教授嘛。本人只是在网上曾经细细看过此公的水墨,当时佩服得那真是快要接近五体投地了呢。于是,我说我肯定去。结果,去了金州之后,这位说好来玩的尹大仙去山东主持自己博士生的画展时间有了点冲突,最终却没能成行。害得老牛兴兴而去,郁郁而返。只恨缘分未到,瞎胡忙活一场。
谁知道,回到牛居窝了二十天以后,令人意外地接到了“黔西南之旅”结识的一美眉电话说,“尹老要去海南写生,邀请您三亚赴会。烦劳放下手头吃饭的营生一同散心,不知有此雅兴否?”一听这个消息,老牛便赶紧又一次装起刷牙缸子,闹得一夜都没睡安稳。结果,大清早去机场偏偏赶上塞车,就差那么十来分钟,飞机驾驶员不管不顾地毅然把飞机开走了。咋办,老牛使用手机只会接打电话,改签哪一档子又不会独立操作,只有默念几声佛号打道回府呗。谁知道,早已飞临海口的美女接到老牛误机的信息,居然遥控换票成功,要第二天赶早重飞一次。还好,隔天登机顺利,空中也未发生空难之类,总算平安到达第一站海口。
这是牛某和尹大师的第一次见面,其庄严场景绝不亚于井冈山那场朱毛会师。酒罢茶余,牛某仔细地将心中偶像细细打量了一番又一番,不禁哑然失笑。两兄弟除“尹老”比“牛爷”年龄小几岁之外,面相却多处雷同,生活情趣相类之处也惊人的毫无二致。首先是光头,浓眉,吃白酒,打呼噜,牙口尚好,热爱女人,特别是最后同一缺陷更是令人十分骄傲——两个人都左耳失聪。
说句实在话,沧海先生的画作除博客阅读之外,真迹此前我还真没能亲眼目睹。说来也是二人投缘,此番匆匆见面之后相隔不久,他亲率几个得意弟子的大型画展在苏北宿迁开馆,老牛这才有幸得见真颜。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要说也只能说点皮毛感受。沧海做为范曾老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弟子,师徒俩的作品,完全可以诠释一句中国老话——名师出高徒。再看沧海身后众多弟子的参展力作,亦可谓登堂入室,琳琅满目,龙飞凤舞,器宇轩昂。
两次见面,鄙人当然有机会观摩先生作画。
但见一个憨态可掬的光头佬,面对墨池时而观纸不语抱肘静思,动辄龙飞凤舞泼墨挥毫,绝似一位胸中自有千万兵的将军,站在沙盘前推演着一场兵不血刃的战争。不一阵子,那被墨和水趸得洒洒洋洋的宣纸上,便一忽儿有了苍遒的怪石,流动的溪水、快活的鱼儿,栩栩的水草……
沧海作画,绝像一场悬念跌宕的形意拳师推演拳法。虽然是一人操作,似乎有两队无形的“影子”在缠绵。双方一来一往,极尽三韬六略。让场外的观战者看得那真是如痴如醉,继而不寒而栗,接着又大汗淋漓。
几天后,在海边的渔村,一行人遇到台风刮倒的一株黄角树。面对一群横躺竖卧在自己家门前留守的老人,沧海不走了,并掏出了速写本。接着席地而坐,开始慢慢着笔。开初,那好好的白纸让他瞬间就闹得墨迹斑斓。不过,尽兴是些横七竖八的线条。绝像我家孙孙拿起铅笔,糟蹋爷爷稿纸那样随心所欲。老牛以为,先生肯定是在画眼前那棵被雷电击燃的老树,那些刀削般的线条一定是枝干的一部分。不一会儿,那“树干”却变成了一张老妪生动的脸。仔细看了,那些无形的线条,早就附着了刻意的心思。而且,老妪和我们一同看着眼前野藤缠绕的破败村舍,眼中透出的那种遭受到的深深巨创,远远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的怜悯可以去比拟……
此刻,老牛突然想起了毕加索。这个十三岁时就开始创作宫廷画的聪慧少年,其作品的老道程度那时候已经活脱脱出自一位老画家之手;只是到了耄耋之年,这个人的抽象画却“抽象”得如同顽童戏墨!让行外人去品味,都不免五味陈杂起来。这,或者就是艺术的体现和召感吧。至少证明,这些堪称大师的人,敢情一个个都是天赋异禀的超人么……?
既然把话说得如此肉麻,不妨再多两句亦无妨。看过老先生珍藏公展的那些作品,老牛有个无力的感慨,归结成一句话,那就是——尹沧海的画作已经不屑于一般美评人那点廉价恭维去说三道四了。如是说这个人已经走入另一个境界的话,它正在等待着历史对一个时代的大作做出最终的评价。然而,做为一个外行的艺术欣赏者,能在有生之年见证过一代大师泼墨作画,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缘分。
鄙人是靠写文章混口的人,沧海是靠作画抒情的人。两个老头吃饭的行道不同,但对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存在都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们坐下来,并不会专门说画,因为老牛不懂画。两人大多都在闲聊、瞎聊,聊着一些别人并不去关心的事情。沧海先生无意中自揭丑事说,上小学那阵子,他在算术课堂也敢画画玩,终于在一次被老师抓了现场。因了他画的是老师,不知道对方欣赏不了他那抽象画笔意,还是他那画多少有点丑化之嫌,当即被老师揪到教室外去反省,闹得好没面子。为之,他拿起书包退学了。大约过了半年时间,可能是自觉参加生产队劳动还不如在学校受老师罚站轻省,便讷讷地向老爷子吐口说出想继续学业的意向。老爷子肯定地问他,你觉得担牛粪好还是上学好,他由衷地认为上学比担牛粪好些。于是乎,他又乖乖地去学校念书去了。由之,尹家大院少了一个放牛郎,中国多了一个大文人。
在中国文人这个行道上,严格地讲来,并没有什么书法家或者画家。拿着毛笔写字那是识字人的基本功,写着写着也就手熟了。琴棋书画也只是生活中的小趣味,他们最看重自己的文章。于是,留世的那些字字画画的背后,那些巨匠全部都堪称是文学泰斗啊!几天相处,先生的仅仅谈吐流露出的学养让鄙人由衷地佩服。即便他很不愿意让人当面称作教授或者“大师”,这个人却在文学、诗赋、书法上有独到的见地和很高的造诣。如此说来,做一个画家,是不是首先得比常人多读些书呢?
我觉得,和先生这样的朋友坐在一起,聆听一番说教,你会以为他是个诗人;动辄提到稼穑之事,又觉得面对的是一个辛勤的农人。当你看见他把一池水墨瞬间化幻成一首如诗般的画,你就会醒过神来,什么才是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