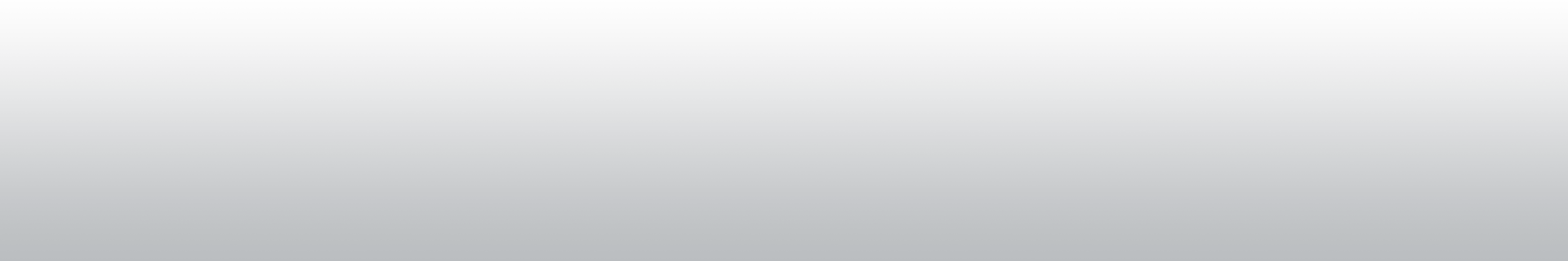刘成纪
2012年10月20日,应南开大学薛富兴教授邀请,至天津观赏尹沧海教授的画作。自从我20余年前开始从事美学研究,中间遇到最多的误解就是人们往往将美学等同于美术。但是,这种误解也有其历史的根据和道理。比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美术泛指一切艺术。如鲁迅1913年《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云:“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f fine art)。”“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苟合于此,则无间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1918年,蔡元培先生在一篇演说中也谈到:“美术本包括有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科。”从这个角度讲,美学作为艺术哲学,虽然它与美术有异,但它最重要的任务却是对美术或艺术现象做出富有理论见地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必然是以对美术的深入领悟、理解为前提的。朱光潜先生讲“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说的就是对艺术的熟稔对美学研究而言具有无以复加的重要性。但可惜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生逢“文革”正酣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艺术教育先天缺乏;后又遭遇制度化的现代学术训练,能把各种哲学、美学理论通读尚且困难,“通一艺”的目标更难以实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能有机会拜访艺术家并借此为艰涩枯燥的美学理论填充生动鲜活的艺术经验,就成为一种让人时时心生向往的“美事”了。
一
尹沧海,1966年出生于“中国书画艺术之乡”安徽萧县。自幼习画,20岁考入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1994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研究生,2000年入读南开大学艺术史专业博士。自1990年起先后任教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现为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也许本人与尹沧海先生同龄而且同出生于黄淮海平原东南边陲地带的缘故,我总固执地相信他的童年经历、所亲历的故乡自然人文风物,对他的绘画产生着持久的影响。从地理上看,萧县属于暖温带气候,它的植被与庄子曾亲密接触并为后世中原王朝的文人歌咏的自然风物几无差异。这似乎决定了尹沧海的绘画,尤其是其中的花鸟画,在题材上永远有着难以掩藏的原乡痕迹。像《此中便与凡尘隔》、《昨夜月明浑似水》中的鸟鹊,《秋酣》中的睡鸭,《识钩否》中的蛤蟆,《性静元如日月明》、《清秋》中的蚂蚱,虽然被画家赋予了种种哲学或宗教的隐喻义,但其姿态、韵致却永远是与其少年时代的乡居经验密切相关的。甚至一些非地域性的自然风物,如荷花、梅花以及形形色色的林木,都似乎在作者笔下被赋予了原乡的印记和神采。这种童年期关于某一国家地理区域的自然认知,作为一种经验范式,总是会对一个画家形成宿命性的规定。说它是艺术家对故乡的忠诚也好,说它是一种无法甩脱的童年记忆也罢,尹沧海绘画中这种自然经验原型是存在的。此后,无论江南塞北什么样的物象进入画面,似乎都经过了这种经验范式的重组或改造,成为原乡经验的延伸物。这就像他以水墨画加勒比海,这遥远的美洲之海也就被纳入中国艺术的话语体系和表现范式、成为纯粹中国风格的西方之海一样。于此,艺术经验成为从故乡出发的经验,艺术创造则表现为这种既有经验范式的不断放大。
从尹沧海的绘画看,除了原乡经验,另一个对其形成重大影响的就是中国画的艺术传统。在当代国画艺术家中,尹沧海是典型的学院派。幼年时期即受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熏染,此后经正规的本科、硕士、博士训练,直至成为国内著名高等学府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无一不是沿着严格学院式的路径摸索前进。看他的绘画,虽然画面意象深具个性,但中国文人画写意的传统是贯穿始终的。托物寄情、托物言意,以有限之象去暗示、呈现无限空�的哲学之境,是其绘画的主导性目标。这种追求,使其绘画迥然有别于西方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而是作为“哲学的圣像”存在。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精髓所在。在绘画技法上,尹沧海熟稔传统,讲究笔墨。10月20日下午至晚间,笔者有幸目睹了他在南开大学画室内的即兴创作。当时运笔如风如电,如舞如练,但在泼墨写意的痛快淋漓中描、绘、皴、擦、点、染,却无一不体现出传统用笔的功力和规范。陈绶祥先生称赞其“于笔墨意境中探求画道”,“于笔墨中遍假古今选用”,是切中肯綮的。这种对传统的继承甚至影响到了他对绘画题材的选择。除荷、梅、兰、竹、菊这些宋元以降文人画常常涉及的题材外,他画的最传神的对象有石榴、兔子、锦鸡、鸳鸯、白鹅、睡鸭、喜鹊等,如《石榴折枝》、《迎春图》、《谁令秋水边,弄月餐清露》、《修羽临风翠欲飞》、《春消息》、《春江花月夜》、《梅林春早》等。这些工笔、写意兼备的作品,不仅表现了作者精细的摹写能力,而且也使中国自五代以降即反复出现在花鸟画中的动植物意象在新的艺术意境中复活。另外,他画的佛画,既推陈出新,又于史有本。像《镜中之影,水中之月》一幅,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佛理禅机的独特领悟,但同时从中不难看出赵孟?《红衣罗汉图》的影子。在当今这个崇尚艺术自由而逐渐将传统笔墨技法、绘画题材归零的时代,尹沧海这种对艺术传统的坚守是值得称道的。当然,这种坚守也使他得到了重要的回报。看他的山水写意、工笔花鸟,无不浸润着一种典雅的韵致,具有高古的意境并弥散着清朗而超迈的书卷之气。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画最为珍视的东西,也是崇尚变革的现代画家最容易遗失的东西。尹沧海成功将这一传统接续了下来,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在中国画史中,工笔与写意似乎是一对永远对立的范畴。前者认为后者技法贫弱,后者认为前者匠气过重。两者的矛盾其实构成了对中国艺术形与神、象与意、再现与表现等诸多对立的一个简要总结。难能可贵的是,尹沧海绘画以写意见长,但他的花鸟也极尽工笔之能。更有甚者,则以工笔、写意并举的方式,将绘画的层次感和表现力推向极致。同时,尹沧海画山水花鸟,也画人物;画细如毫发的鸟羽虫臂,也画气势恢弘的大幅山水。这种多专多能、能屈能张的画家,在当代艺术家群体中是不多见的。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源自他研习传统得来的积厚之功,另外当然也离不开他在高校中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强迫性。所谓学院派,大概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熟稔历史,博今通古,否则专以一技之长应付学生,那真是要误人子弟了。
二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谈到古希腊艺术时曾讲,古希腊时代并不存在其雕塑中表现的美男子。这些雕像的美,只不过来自石匠或艺术按照他们世代相传的技术进行的图式化制作,即:“我们要是能看到亚里山大大帝的一张快相,很可能发现它完全不像那个胸像。莱西波斯的雕像可能很像个神,而不像那位亚细亚征服者本人。”“艺术家不过是勾画一个程式化的形象。”贡布里希的这种看法,对理解中国传统绘画以及艺术家与传统的关系是同样适用的。自南朝时期山水自然成为中国画的主要摹画对象以来,无论其表现技法还是题材都日益程式化,所谓的意境、笔墨问题也日益成为不可撼动的铁律。这种现象,遂使后世艺术出现了有法与无法、师法古人与师法自然的尖锐对立。在当代,吴冠中先生“笔墨等于零”的讲法看似偏激,但在今天这个凡事讲求创新、反传统构成了主流传统的时代,却恰切反映了艺术家在面对传统这一重负时内心时时泛起的焦虑。
比较言之,在当代画家群体中,尹沧海应算是在继承传统与追求创新之间比较折中的一位。从其业师陈绶祥对其作品笔墨、意境的肯定以及他对陈绶祥“新文人画”的推崇不难看出,他不但对于传统不抱敌意,而且将其作为国画艺术必须继承的传统和依重的资源。关于尹沧海绘画的特点,评论者魏宏远曾言:“尹君画多取‘常态’,不论人物、花鸟、山水,都能从‘常’中取静,从‘常’中寄深情。”这里的“常”,我想一个十分重要的面向就是他在笔墨技法上顺随于传统,画中物象也大多见于前代画家的作品或日常生活中的习见之物。但需要指出的是,尹沧海绘画中的“常”,只不过是继承了中国绘画传统的“常道”,这一“常道”使他的人物、花鸟、山水表现出与艺术历史的深刻关联,并因此于史有本,但并不意味着他缺乏创新或者食古不化。恰恰相反,正是有传统作为厚重的依托,他的变革才摆脱了名利场中的花拳绣腿、虚张声势,体现出更具深度也更势大力沉的颠覆性。只有真正理解艺术历史的人才能再造艺术的历史,这对尹沧海变革传统、自创新局的努力应具有准确的描述力。
那么,尹沧海超越传统、自创新局的路径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他自己曾在其画论中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其对于绘画之法既应有在学的过程中的‘益’,也应该认识到绘画的终极不是单纯的法的增益,而应该在法度完备的情况下‘损之又损’,直至达到内心的纯粹表达,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尤其在当代,各种奇巧淫技扰乱人心,让人在‘法’的变化中迷失自然之性,‘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坛经·行由品》)。‘人得一以宁’(《老子》),所以‘有法’、‘无法’只是在特定的时空下对待创作的一种态度,争论并无重要性可言,如果能复归古典精神,复归于朴的单纯,那么,就不会囿于‘有法’或‘无法’的执着。”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所谓创新并不是尹沧海为之焦虑的问题。在他看来,技法不重要,内心的纯粹表达才最重要。无论师法传统还是背离传统,这种讨论只不过涉及绘画技术的层面,真正的问题是超越技法之上的心灵自由。有了自由无碍的心灵或自性,所谓的法则就会成为人役使的工具,而不会成为人自置的囚牢或樊篱。在此,尹沧海显然试图在关于创新的技术性争论背后找到一条更具本质性的道路,这就是以当下的自由心灵纵贯古今、然后自创新局的第三条道路。
正是有了超越法度之上的自由心灵为依托,尹沧海的绘画处处可见传统的影子,但又处处显示出超越传统的巨大能量。以其“大画”《行禅图》为例,整幅画以勾线或近似素描的方式展示了一种田园诗式的乡村美景,房舍、竹篱、残桥、山石依次清晰地进入画面,甚至有近似工笔的鸟鹊在树石之间盘桓。但在这清晰的田园风光之间,却时时有大朵大朵乌云般的浓墨涌现出来。这种浓重的墨团,不但使画面在黑与白的张力中强化着表现力,而且也使人领悟到,似乎在一切有形背后漫溢而出的虚无才构成了世界的本质力量。它给予了画面一种无言的纵深、一种喷薄而出的动感、一种与日朗风清相交叠的波诡云谲。而所有这些看似平淡实则奇伟的人间风景,一位远行的禅僧只留给了它一个背影,这到底预示着什么?是要表达一种“生活在别处”式的理想主义的果决,还是一位弃世者对世间好山好水的深深绝望?是仅仅以行走的姿态表明一种精神的态度,还是任何解释都背离了禅宗“不立文字”的隐密?总之,似乎任何解释都有道理,但任何解释都会因诉诸文字而堕入第二义。于此,只能说画家用他的无言,给观画者留下了无尽的惆怅和迷惘。这是一个迷局,但也正是这种迷局化的处理,将观画者对禅的理解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尹沧海另一组极具创意的作品是关于加勒比海的写生画,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在题材处理上的无边界性。水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不可或缺的元素,但这种水多是山中溪流飞瀑,或者江河湖泊,甚少有中国山水画家画海。尤其西方的海,似乎更是被西方油画家独占的领地,任何人染指这一区域,似乎不但因其侵略性而触犯了中国人历来遵守的艺术道德,而且也会因其碰触了似乎不应碰触的题材而在艺术上被视为不伦不类。但是,尹沧海显然没有考虑这些,而是一任自由心灵的指引,将中国画的摹写对象拓展到了无限辽远的国界之外。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笔下的加勒比海,海中的渔船既类似于传统山水画中的文人酒船的造型,又多了几分西洋式的质感和坚硬。海中的波浪曲线,既因深海的独特颜色而显出柔韧和凝重,但同时又保留了国画写意的特征。那向远方延伸的海天一色的天际,则纯粹是中国性的,它用迷离朦胧的混合表达与西方永远清晰的焦点透视法拉开了距离。总之,尹沧海用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再造了加勒比海,使这一远离故国的区域以艺术的方式具备了中国性。近代以来,自郎世宁始,只有西方艺术家不断蚕食中国这片中国本土艺术的专属领域,绝少有中国画家以艺术的方式实现对西方的“占领”。尹沧海将加勒比海纳入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版图,这显然是在艺术题材上的一大开拓,也是以中国本土艺术为主体成功实现的跨文化实践。可以想见的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和艺术家民族自信心的增加,中国山水画绝不会将其题材永远限定在国土疆域之内,而是会跨越有形的地理边界和无形的心理边界,向更趋辽远的区域蔓延。有朝一日,可能整个世界都会被中国画家以写意山水或花鸟的方式重新赋形或改写,这也是中国艺术获得世界地位和影响力的具体表征。在这方面,尹沧海无疑以他超越法度的大胆和心灵的无界,成为值得钦佩的先行者。
三
中国传统艺术有两大精神支柱,一个是道家,一个是儒家。一般而言,道家的“畅神”观念影响了中国的山水艺术,儒家的“比德”则使花鸟画成为人的德性的比附或象征。但是,自宋代文人画之后,花鸟画渐渐出现儒道杂合的新趋势,画家笔下的花鸟鱼虫不仅作为人物情感、节操的兴寄之物,而且也渐渐追求散逸,高妙与自然,即从托物言情、托物言志走向了托物言意。这种趋势,使花鸟画摆脱了摹形状物的工丽纤巧,向更具哲学意味、更彰显心灵自由的水墨写意发展。同时,中国画的山水人物,自魏晋时期即受佛教的影响,至唐五代时期则以禅宗为主导,形成对绘画艺术的全面进入。就哲学取向而言,佛禅与道家既相契合又相差异。契合在于都是在绘画的视觉传达之上为艺术设立了更高的哲学目标。甚而言之,道家和佛禅都是反艺术的,但它们均以反艺术深化了中国艺术。差异在于道家以有无、阴阳等影响了中国写意画对虚实、黑白的选择,禅宗对艺术的介入则主要源于它对世间万象的存在论反省。这种反省,使空色问题成为艺术的核心问题。其中,空的价值在于营造画面的空蒙明净之境,色的价值在于给画面一种“活泼泼的”的亮丽和生意。从画史看,儒、道、禅围绕艺术的汇聚是从中唐时期的王维开始的,自此以降,中国的写意山水和花鸟,既儒且道且禅又非儒非道非禅,三者的互补、融会,使咫尺画图,成为哲学的永恒隐喻和象征。同时也使传统哲学成为画家必修的功课。
在当代中国绘画界,以自觉的哲学意识面对自己艺术创作的画家不乏其人,但能达到尹沧海精神境界的则极少见。从其厚厚的两本画论集可以看出,他不但是一位画家,也是一种学者;不仅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靠“立象尽意”的思想者。如在以《画余赘语》命名的一组短章中,作者讨论了中国文人写意画的水墨、儒道禅的不同取向及会通、元气自然论及中国画的虚实恍惚等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绘画以水墨为格,画中设色的意义仅在于补笔墨之不足,显笔墨之妙处。“‘笔墨’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绘画语言,更是融儒道释为一体的中国写意画的精神之所在”。受水墨写意传统影响的中国画尚淡、尚静、尚纯,以形为载具,以诗为魂魄。正是因此,这种绘画虽然需要物质性的载体,但本质上是“非‘物质美’的,蕴含着更为深广的人文内涵”;它需要凭借形象形成审美的传达,但它在根本意义却否定形象,形的意义只是“用来表现无形的精神”。这类论述,看似更多涉及对绘画形象的技术处理,但它在超越的维度却触及到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或者说,它以艺术为媒介,打通了一条走向哲学的道路,反向也使他的艺术创作成为哲学观念的映像形式。
尹沧海在艺术创作中达到的哲学自觉,也鲜明地表现在他的作品题款及具体艺术创作过程。首先,以《中国美术家作品集·尹沧海》中涉及的画作为例,其中许多作品只是勾勒了生活中习见习闻的花鸟鱼虫之属,但其题款却别开气象和意境。如作于2004年的一幅墨荷,被命名为《诸法空相》,同时抄录了一段《金刚经》文作为款识;作于2007年的石榴图,被其命名为《性静元如日月明》……。这种题款,初看似乎存在形意之间的错位,但按照《金刚经》“于相离相”、“以喻为筏”的接引法,却有效地通过至常至减的日常物象实现了对绘画精神格调的提升。其次,2010年10月20日的天津之行,笔者具体观察了尹沧海的绘画创作过程。如他画一幅写意梅花的程序:先用排刷式的大笔挥出梅花苍老朴拙的躯干,然后尚着躯干的走势以淡墨描出几朵镂空的花瓣,最后则以棕黄与红的过渡色为花朵作似有还无的点缀。这一图绘过程,表面看来不过是一种画面处理的技术,但在本质上却表现出传统哲学在中国写意画中所占据位置的先后和主次。其中,用浓墨挥洒出的老梅的躯干,纯任黑白二色,这对于画面是奠基性的,它标示着道家由有无衍生出的黑白问题,构成了中国水墨写意画的原色和主干。然后,以淡墨描出的镂空式花瓣使画面见出一种俊朗而有韵致的精神,这关乎性灵,近于儒家试图以梅花暗示一种高洁的人格。最后,简单的色彩点缀,则赋予画面一种醒目之感和生动之趣,这近于禅宗试图从微观物象中发现一种“活泼泼”的精神和对无限空色世界的暗示。“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最少的着色其实也就昭示着色相世界的无限敞开。据此不难看出,作者对梅花描画的程序性,其实也代表着道、儒、释在中国艺术中占据的不同位置。从道家的自然性奠基性,到儒家的社会性蕴含,再到禅宗的形而上飘逸,为中国艺术标示了一条不断攀升的哲学路径。而尹沧海则借画梅的演示,对这一哲学上升之路进行了形象的图解。
但是在儒、道、释三者之间,对尹沧海画风影响最巨的莫过于佛教和禅宗。在他的画论集中,最有份量的一篇论文就是在专论禅宗写意画。他曾讲:“把禅宗写意画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审美取向提出来,并非有意在传统学术界普遍承认的‘文人画’和‘院体画’之外又加一个‘禅宗写意派’,只是意在指出影响水墨写意画风格演变过程诸因素中,‘禅宗写意画’比前两者似乎在艺术语言与思想上更能说明问题之所在。”这段话虽然说的委婉,但依然难掩尹沧海在绘画理论上自我论证的企图。从世纪之初以来的绘画实践看,佛禅在他作品中留下的印迹是最明显的。画面的明净和疏朗,枯枝碎叶闲花的空灵之相以及鸟鹊的生趣、布色的亮丽甚至挑逗性,均不是执着于哲学有无问题的老庄所可给予,而只可能源于佛禅的空色关系。或者说,即便他在画论中反复提到老庄,并贯彻于绘画实践,但这也不是原初意义上的老庄,而是被禅宗以明净之境纯化、照亮的老庄。就这个意义而言,虽然在技术层面可以为其绘画实践设定出一个从道到儒、再到禅宗的程序,但禅对于尹沧海却不是可有可无的余物,而是以其空灵之境实现了对于道与儒的反向改造和贯穿。也就是说,他的绘画表现的并不是道家、甚至儒家的真精神,而是一种被禅宗化的精神。
截至目前,佛禅精神在尹沧海绘画中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迹见于他与“月下”有关的作品中。与道家哲学主静不同,佛禅主净,而大千世界的明净、澄澈、静寂、空幻、一体之感,则在镜花水月之间找到了最佳象征。作为重要的喻体,月印万川即预示着佛教的真如之境。如《佛说月喻经》云:“如世所见,皎月圆满,行于虚空,清净无碍。”“今我所说,犹月行空,清净无碍。”关于这一世界的空幻,《维摩诘经》则云:“诸法皆妄见,如梦如焰,如水中月,如镜中像,以妄想生。”以这些佛教经卷为背景,中土的禅师与参禅的文士,则借“一朝风月,万古长空”来体验世界的空幻与永恒、佛法的圆通无界与瞬间的人生趣意。如唐永嘉玄觉禅师《证道歌》:“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宋姚云文《八声甘州·竞渡》云:“人声断,虚齐半掩,月印枯禅。”元王沂《宿观意寺》诗云:“紫罗山口梵王宫,一树凌霄自在红。我悟色空心似水,禅床闲卧月明中。”明道�《题泉月图》云:“月明影在地,泉清光彻天。何须分上下,空寂是吾禅。”清无名氏《赠扫叶上人》诗云:“拈花久碍人天眼,扫叶犹留解脱心。何似无花并无叶,千山明月一空林。”可以认为,尹沧海是这一贯穿佛禅史的明月主题的当代参证者,他常以“明月沧海”自名,便是这种一月映照古今的印证。在他的画作中,最给人带来心灵震撼、也最显现创造力的作品多与月有关,极具代表性的是《天华峰月光下写生》系列。如其中的“之一”和“之一”,画面的光影处理极见慧眼,明月昭昭,如水银泻地,光被华林;天地分辉,河山共影,呈现出表里澄澈的明净之境。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画中林木以其庞大的冠盖和参差的树干共同营造出的“林中空地”,月光在其间穿行,使林中世界明净通透,一览无余,直至光影掩映的画面纵深。在中国古代,起码自李白始,向来不缺乏吟咏明月之美的诗人,但以月下世界为题材并藉此兴寄哲学和宗教情怀的画家却不多见。尹沧海将这一世界之美表现得摄人心魄,既是他独辟蹊径的创造,也是他标举的禅宗写意画至目前为止的巅峰之作。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画家中,尹沧海是惟一配得上“月光画家”这一称谓的人。
四
以上就是天津一日的观画经验。虽然时间短暂,认知有限,但从中已可以看出尹沧海让人叹为观止的多元性和不拘一法的艺术创造活力。中国艺术是终生的事业。西晋人陈韪评价孔融时讲:“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唐孙过庭《书谱》讲:“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所以我想,在一个国画家正值盛年、艺术生命的蓝图华光初照之际,说他已达至顶峰或化境之类,这种过誉之词,看似赞美,实则是对其未来艺术前景的看衰甚至诅咒。但是,对于尹沧海,任何过苛或过誉的评价,都无法掩盖其作品中已经显露的夺人眼目的大家气象。
首先,这种气象源自他的原乡自然人文经验。如上所言,尹沧海20岁之前生活于安徽萧县,他少年时代所闻所见的自然人文风物,是与起于中原、以妙造自然为主题的中国山水花鸟传统天然接续的。一轮明月通照今古,一花一草岁岁年年,中国传统绘画围绕中原这一地理区域形成的自然经验范式,与尹沧海的童年经验不存在任何龃龉。论者之所以说他的画中人物、花鸟、山水“多取常态”,正是因为传统中国画家起于中原的自然经验,构成了中国艺术的“常”。同时,萧县南通江浙吴越,北依齐鲁燕赵,这也使尹沧海画中的自然以“中”与“常”为基点,体现出向南方灵秀与北方质直双重风格的渐变。这种“常”与“变”关系,是尹沧海画风多样性的自然基础,也是国家自然地理给起于萧县的龙城画派的天然恩赐。
其次,这种气象源自他对中国画笔墨传统的积年研习和继承。尹沧海作为一位以写意为主的国画家,他的工笔纤巧精致,在当代写意画家中几乎无人能及。这种写意与工笔的混搭,往往使他的作品亮人眼目,别出新意,但在根本上却是对他花在艺术传统中的积年之功的验证。同时,他的画作中渗透的古意以及时时逸出的书卷之气,更是见出了传统文人写意画的真精神。现代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学院派画家都是艺术传统最坚定的捍卫者,但在这个患上了创新焦虑症的年代,他们也往往因为执着于传统而时时招致不屑和敌意。如20世纪初叶,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帕拉采斯基曾尖刻地讲:“把那些批评我们的教授关进疯人院,让他们在那里进修。”但显然,对于中国画这一独具自身的程式、题材、精神因此与西方判然有别的艺术形式而言,学院派就是中国气派,坚持传统就是坚持艺术的本土性,就是对无所不在的西方化或全球化浪潮的无言的抗拒。同时,任何艺术创新都是基于传统的创新,否则“创新”将因失去“继承”这一相反相成的命题而在逻辑上讲不通。尹沧海的绘画是于史有本的,这种历史意味和书卷式的静气,与这个被变革欲望催生的、让人眼花缭乱的艺术时尚世界保持了距离,但也正是这种距离,使其艺术呈现出一种艺术的常道,一种时时可供人栖息的精神家园。
第三,这种气象源于他备于传统而自开新局。从尹沧海的求学之路、教书生涯画中笔墨意趣以及充满真知灼见的画论,固然可以看出他是中国文人写意传统在当代的接续者,但从他的艺术实践看,这种对传统的沉潜并没有成为他艺术创新的重负,相反,却是他基于传统而自创新局的强大支撑。关于这一问题,庄子在其《逍遥游》中曾以水舟、鹏鸟之喻,说过下面意味深长的话:“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这段话说明,水的深度决定着它对舟船形成何种样式的漂浮,风的厚度决定着大鹏高飞远举的广远。艺术家也是如此,任何创新都源于他在传统、人生、世象诸方面的积厚之功。惟有如此,他的创造才会势大力沉,才能行之久远。尹沧海正当人生盛年,便依托传统积淀而不拘于传统,表现出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到他“人书俱老”的时日究竟会有如何的成就,这确实值得等待,让人期许。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作者简介:
刘成纪,男,河南虞城人,1967年2月生于陕西铜川市。郑州大学中文系本科、硕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美学专业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博士后。1997年晋升副教授,2001年晋升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美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价值与文化中心研究员,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编委。兼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教授,澳门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国际美学协会会员。曾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短期讲学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