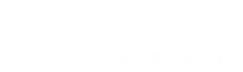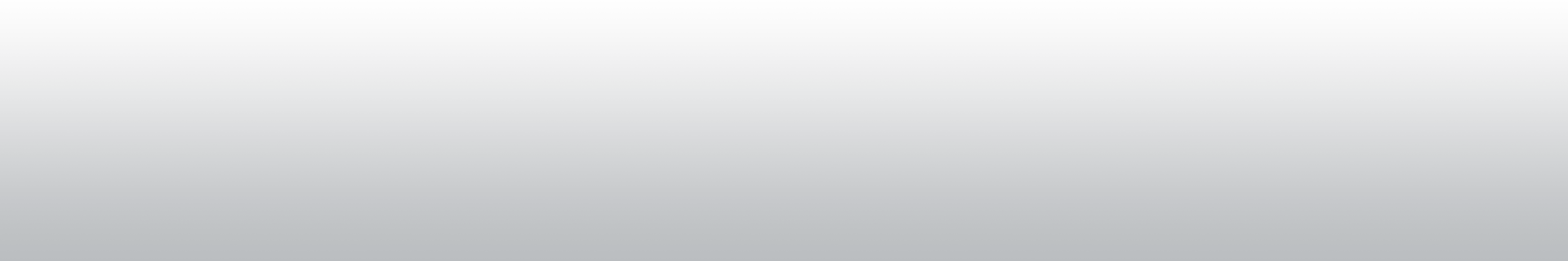韩德民
提要:20世纪90年代之后崛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决定了中国画创作领域主导话语从“改造”到“回归”传统的转换。对这种时代主题转换的自觉认识和坚定认同,使尹氏艺术创作道路避免了诸多可能的弯路,但真正导致其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还在于他从自己实践出发所达到的对“师古”和“自作主宰”关系的切实领悟。尹沧海人格意识中的乡村情结,及乡村意象在现代化背景下赋有的准宗教性文化属性,给他的运笔构图提供了某种有别于传统士大夫情怀的深层生命动力。就未来发展言之,这种人格精神侧面,也可望为其进一步的拓新求变,提供强有力的内在心理支持。
关键词:尹沧海;文人画;乡村信仰;文化保守主义
作者:韩德民,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文化交流系主任
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五四”时期兴起的全面反传统思潮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尽管形态方式和功能性质都不尽相同,仍然可以说《河殇》等所代表的那样一种彻底告别中国固有文化观念体系的冲动,甚至和“文革”时期相比也并不逊色。但也正是这种全盘反传统倾向的登峰造极,激发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复活与曼延。反映到中国画创作领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复活的表征之一,就是新文人画运动的风生水起。受庇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主流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以徐悲鸿等为代表的要求参照西方写实主义观念对中国绘画进行“改造”的主张,逐渐演变成了艺术界的“政治正确”,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敢于与之正面抗衡。受制于这种“正确”的思维定势,前后延续数百年,本是作为中国画主流和最高成就体现的文人画传统,逐渐被贴上诸如“颓败”乃至“病态”的标签,成为备受冷落乃至鄙弃的对象。受到文化与政治领域内重新崛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维的鼓励,新文人画运动开始反省总结中国画“改造”运动的是非得失,并尝试以同情之态度重新认识传统的内涵及其在现代艺术创造过程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
作为基本艺术理念奠定于此一时期的年轻艺术家,尹沧海以自己的方式响应了时代精神主潮的这次转向,20年来逐步走出自己一条以继承为创造、从承传中求开新的探索之路。这种以复古方式克服现实弊端的创新策略,无论中西历史上都不乏其例。尹氏有丰厚的理论素养,其于中国绘画的审美属性有自己的领悟:“国画之所以存在并区别于其他画种,即在于它绘画语言的写意性,而这种写意性又源自中国传统之文化观念,是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衍化发展的产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执着,老子‘善行无迹’的自然,庄子‘解衣般礴’的气势,以及佛家‘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超脱,都给予中国画艺术以深厚的意蕴,其思想内涵与审美取向构成了传统绘画的基础,所以,中国画的写意性又必须区别于西方的表现主义。……中国画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自然物象深刻体察之上的一种高度凝练的情感表达。它的写意性使人、社会、自然三者在绘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从这种理解出发,他对美术界的许多流行现象表达了自己鲜明的否定态度:“从多年的展览状况看,现代水墨画大都带有‘前卫’、‘实验’、‘POP’‘艳俗’等倾向。他们对古典美学进行破坏,追求外在的视觉效果,抛弃传统笔墨语言,多以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硬边主义、构成主义、极少主义、波普艺术等等作为形式语言母体。由于他们所谓的国际态度,单纯强调水墨的材料特点而非民族文化特质,认为仅仅在材料上保持与传统的某种联系即可,这实际上是勉强的‘嫁接’。”在对流行现象的否定背后,是涵泳消化传统滋养的长期踏实努力,由此而有其学养与人格气象的日渐通达,每令观者有“奇异”之叹。这种自觉的修养功夫是尹氏绘画境界提升的坚实基础,使其有可能从根本上区别于拘执在单纯“画艺”层面的诸多匠师型画家。
张�自承作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历代名画记》),形式上看是“中(内”)“外”、“心源”与“造化”对举,实则内外同归乎心。中国文化观念中的“造化”,所指并非形而下的具体物象,而是“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庄子·田子方》)的自然生物之元气,能够与此种通乎“道”的元气相摩相荡的,必是超乎感官知觉之上的“神”,所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盈天地间只是一个大生”(罗汝芳《盱坛直诠·上卷》),无论“造化”还是“心源”,鼓荡其间的,无非天地宇宙的生机和生气,但这生机与生气,又只有借心体的空灵才能进入澄明,才能从“生”之晦暗达于“生”之莹彻。“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造化的精神有赖于艺术家的敏锐予以警醒;反过来,“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马祖道一语录),心灵的朝彻,也有待于造化的启迪充实,否则就只是空而不成其为灵。不灵之空映照不出实有的渊深混沌,甚至最终将沉沦为其渊深混沌的一部分。王阳明就此总结得非常透辟:“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体。”(《阳明全书·传习录下》)尹氏对中国绘画主流传统的回归与认同,表现在思维方式层面,就是从其实际创作经验出发,以自己的方式反复印证“造化”和“心源”这种“原是一体”的关系:“在创作过程中,他所观照的,已经不再是花的详尽的细节,一些枝节的真实已经被精练的笔墨韵味和独立的审美特征所消解,画面上体现的是它整体的形象。”“心”的本体地位通过笔墨本身独立审美韵味的突出而渐次取代外在物象成为表现的中心,这正是历史上文人画取代院体画开始成为中国绘画主流的重要标志。
就命名中国绘画艺术营构的观念资源言之,尹沧海对儒释道诸家传统实际上取兼收并蓄之态度。对应于儒家君子理想的梅兰竹菊系列,是他不同时期反复介入的题材之一。《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2011年)、《居高声自远 非是籍秋风》(2006年)、《踏雪寻梅》(2006年)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让形象创造借儒家伦理理想获得意义提升的趣味偏尚。借用道家思想元素的个案,比较典型的如《大音希声》(1992年)、《心闲便是神仙》(2005年)、《空山松子落 幽人应未眠》(2005年)、《清流濯足图》(2008)等。至于体现禅悦之风的选题和构图方式,在其每个时期的作品中都可以说是随处可得。当然,这样的分类列举,仅仅是要强调,画家怀有认同并多方面推介传统价值理念的强烈意愿。就具体作品的主题把握言之,儒家视野中的坚贞廉正,道家视野中的超逸高洁,佛教思维中的空明通脱,实际上相互间通常很难划出明确的分界,而更可能呈现为相互渗透融汇的关系,因为宋元以后,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情怀通常都是儒释道三种传统共同塑造的结果。
二
梁漱溟比较文化之中西差异,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即在于它是一种“心的文化”。孔子“以仁释礼”,将中国文化的重心从外在规范制度移转至于内在精神价值之建构,孟子沿此趣向,确立起儒家之心学传统。相比孟子,庄子予道家自然无为之道以心灵境界化处理的倾向更明显。佛教东来,最初民间视之为神仙方技之一种,但进入上层主流社会后,很快追求目标即从升天成佛转向“见性成佛”,“心宗”或谓“禅宗”之最后成为中国化佛学的正宗,与佛教传统本身的价值关怀方式固然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更多地还是中国本土文化内在逻辑演进的结果。儒道佛各有其渊源的心学化致思方式,到宋明时期共同汇聚于理学观念体系,有力地形构了士大夫阶层的心理趣味和整个社会的精神风尚。陈寅恪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种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文化”,陈氏认为其最突出标志,就在于“尚气节而羞势利”,所以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脱心志于俗谛”就是要心灵“自作主宰”,所以说“夫学贵得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阳明全书·答罗整庵书》)审美意象作为艺术存在的本体,当然是主体与对象相互呼应和融合的结果,但就其融合的具体方式和形态呈现言之,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趣尚却可能导致很大的差异。欧洲绘画之总体上以写实为基本创作路径,而中国绘画之终于走向重笔墨而轻色彩、重写意而轻造型的道路,从根本上说即是受这种强调自我意识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趣尚影响的结果。王世贞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艺苑卮言》)也说的是意象形态这种因主体自我意识变化而形成的具体构成方式上的改变。阳明诗曰:“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边寻。”(《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之三)梁任公发挥此意,撰《惟心》之论,其文曰:“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既一切物境皆心境,则当然上乘艺境之经营必最终走上写心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山水画从早期属意于“度物象而取其真”(荆浩《笔法记》),终于走向“不求形似求生韵”(徐渭《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漱老谑墨》)的写意道路的内在逻辑根据。
在多样化的文人写意传统中,沧海对徐渭和八大山人似乎表现得格外情有独钟。沧海造境,每每追求墨迹淋漓、振聋发聩的效果,兼之笔法狂放、纵横睥睨,故其画风识者每以“奇崛”、“非常”呼之。《昨夜月明浑似水》(2005年)、《此中便与凡尘隔》(2010年)、《阳朔之秋》(2011年)等,都算得上是将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的上乘之作。写意传统的根本,不仅在不拘于物象,更在不拘于法度常规而“自作主宰”,那么当这种不拘法度的精神本身呈现为某种传统或说“法”的情况下,应该怎样理解创作实践中“我”和“法”的关系呢?就此沧海不仅通过创作实践予以摸索,而且以理论思考的方式进行总结。他敏锐地指出,尽管郑板桥自称“敢云我画竟无师”,“事实上,其对于传统,一向是心摹手追,我们从他的兰竹中大都可以看到宋、元、明,乃至他同一时代的画竹、兰妙手之痕迹”,所以“扬州八家提倡‘无法’之论,往往意在矫枉或故弄玄虚”。他根据自己的实感得出结论:“有法与无法对于一个写意画家来说,是取决于创作时的创作心理状态和技术熟练程度造成的心手相应的境界。开合、疏密、虚实、章法、韵致等因素因特定需要而定。切不可把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自由状态看成是胡涂乱抹,因为其创作者的所谓‘自由’也是有度的,其点画披离的‘自由’创作状态是在其‘时见缺落’中显示出文人写意画家的高华之内质。”依这样的认识去实践去探索,无怪乎识者谓之为“有写意能力的人”,以区别于“家家石涛,人人昌硕”了。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素材主题之拣择言之,“造化”指向“天下奇峰”;而在笔墨技法运用层面,“造化”更宜于理解为“师造化的古人”。对于创造来说,真正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摆出反传统的姿态,不在于是否与古法、他法、一切法切割,而在于是否具备“法为我用”或说不以“法”为意的内在运化之功。历史上真正伟大的创新,并没有因其所取的复古姿态而被埋没;反之,貌似横空出世的自我作法,也不可能单靠其背对传统的猖狂,而避免沦入“荒谬绝伦”。基于这样的对“法”与“我”关系的理解,沧海不仅对古人,对写意之外的其他画风,而且对西式技法、选材路向及表现效果,也都不排除借鉴的尝试,这在其近作《加勒比海写生系列》(2012年)及上世纪90年代的《高昌古道》(1999年)等作品中,都有所某种表现。这些借鉴和尝试,对于其多方面地开发水墨大写意画路的现代表现力,应该说都有可能发挥积极的助益作用。
三
论者观沧海以为,“青藤的落拓、八大的冷傲、虚谷的寒峭,却被他以‘了然物外’的‘欢喜心、清净心、平等心’化而为清峻朗润,如‘春风奏和鸣’”。文人画就其主流风格说,往往以荒寒萧索为怀抱之所寄托。相较于历史上的不论倪云林,还是徐渭,或八大山人、石涛,沧海的绘画空间都明显地消减了某些苦寂乃至沉痛,而多出了几分平和生趣,这种情趣神韵上的微妙差别,我以为其实应该也和沧海的个人阅历背景有关。在他2010年4月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乡村还是如此静谧,太阳暖暖地照耀着我的村庄。家门口几株竹子在微风中摇曳,两只绵羊在悠闲地吃着草,院子周围被许多高高的树围绕着,有三两个鸟巢在上面。老母亲就端坐在门口晒太阳。”读着这样的文字,我甚至臆想,“我的村庄”其实才是沧海灵魂最深处的皈依。笔者也出生在那片曾以盐碱著称的土地上,我其实很清楚那片土地上的乡村共同体历史上曾承受过的贫困和现实中正遭遇着的衰败,但透过沧海的文字,我体会到的却是魂归之处的喜悦和宁静。在其另一篇题为《母亲 艺术 平常心》的随笔中,沧海感叹:“从落日的余晖中,从深巷中踌躇走过的老人的背影里,从我儿子的眉宇间,从我无助的企望和收获的喜悦中,母亲无处不在。……那些艰涩的日子,无疑是命运给予我的特殊的亲昵。”如果说悠久深厚的文人画传统及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方式,引导了沧海对于绘画与艺术的基本理解的话,作为补充,我认为,还应该说乡村和土地的气息最初塑造了沧海精神生命的底层结构。因此,融合着乡村智慧的对于乡村的梦想,同儒道释观念所联系着的精英文化传统一样,都是透视其绘画空间精神属性的重要参照。
对“归园田居”主题的吟咏,至少从陶渊明时代就开始了,但乡村意象的文化蕴含,对生活在现代中国的尹沧海,与对徐渭、八大山人等传统士人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性。徐渭等作为艺术家对世俗的精神抵抗,几乎是必然地只能导向避世出世的佛老。在那个时代,乡村社会毫无疑问地仍然是世俗礼法世界的一部分。但在推土机已经将乡村转化成了几乎只是传说的时候,“我的村庄”却可能扮演起类似宗教的角色,能够发挥作为城市社会的批判工具的功能。乡村作为信仰当然有它不同于佛老或说禅的特殊气质,乡村多出了某种基于实用理性的乐观与积极、敦厚与平和。沧海在《几句心里话》里自承:“在我童年的时候,……总是听母亲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于是便读书、读书再读书。然而当我终于完成了爹妈的愿望,生活在这个熙熙攘攘的都市里时,却又不知昨的,总像是没有根的感觉。”这种感觉,我相信是驱动其“画自己喜欢的画”的很重要的心理动力,也是使得那些他“喜欢的画”与纯粹的士大夫情趣有所区别的秘密所在。翻读《太白书屋》(2009年)、《后窗偶得》(2011年)等画作,虽用笔瘦、硬,然老干新枝间鼓荡着的那种峻朗或生意,同倪云林、石涛等类似选材作品透出的枯冷、缄默,构成了很大的反差。支撑这种反差的,使作者能够顽固地体会到即使是枯冷背后的生意的心理力量,或许就是自幼濡染的那种对生命朴实的执着与热爱。这种力量在其某些乡村人物速写中,也曾强烈地触动了我。
不自禁地又想起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记者采访放羊娃,询问娃娃为什么放羊,娃娃说放大了卖钱。记者问卖钱做什么,娃娃说卖钱娶媳妇。记者问娶媳妇做什么,娃说娶媳妇生娃。记者问生娃做什么,娃说生娃让他长大放羊。记者问放羊做什么,……城里人当然可以从这里读出乡村的愚昧和值得同情,但我体会到的却是乡村文化逻辑的直截了当和简洁质朴,是许多所谓远大目标终极意义在这乡村逻辑映照下所可能透出的虚幻和迷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愿意相信,沧海人格结构中的乡村信仰,对他艺境创构的进一步拓新求求,将能够发挥重要而正面的推动作用。
韩德民,男,1964年12月出生,籍贯安徽淮北。哲学博士,现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和中国思想史。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国际美学协会会员。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发表论文有《从救世到混世的精神流变》、《当代美学四派理论视角的考察》、《李泽厚与二十世纪后十期中国美学》、《传统文化的危机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反文化思潮》、《回归“中体西川”》等60余篇。出版有《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孝亲的情怀》等著作,主编有《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