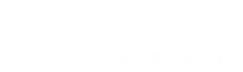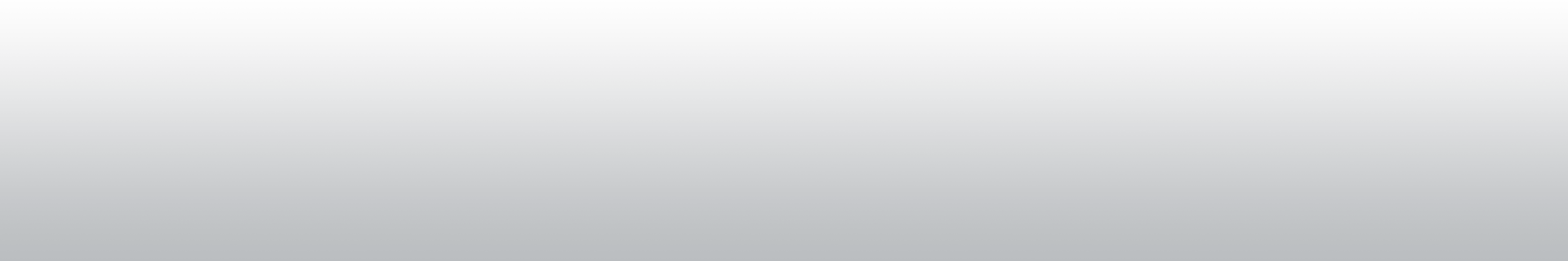刘顺利
从1985年参加天津市美学学会的工作,又由于美学会秘书处长期设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我与天津的画家、书法家的交往不算少,看的绘画就更多了,尤其是看范增先生的绘画最多。当然也看过别的作品展览,包括八大山人的作品,也在王国维所说的“经眼”之列。但最近十几年,已经好久没有看画家现场作画了。这次有机会观摩南开大学尹沧海教授现场作画,我的心情很激动,甚至有些亢奋。
每次看国画画家的表演,对于我这个学中文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国学的熏陶。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色彩。
在我看来,国画只有三种色彩,乃是对于曾经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华夏国、华阳国、华胥国等“三华”历史的复现,也是对尧、舜、禹以及夏、商、周上古历史的追忆。
画家使用的宣纸,是至今没有办法在中华大地之外的地方生产的一种特产,尽管有些邻国用尽一切办法把造纸方子搞到手,依然无法如愿,因为这是与材质、气候、温度、湿度甚至化学结构等诸多因素相关的一种产品。宣纸是一种白色,也是国画的底色。白色的纸张与画家使用的墨形成了“黑”与“白”的对照,也暗示了这里展示的乃是从“色彩的极致”到“色彩的归宿”之间的最大多数的色彩组合。画家最后在画面上加盖的印章是朱红色的,而这种色彩本身又是色谱中最中间的形态,它们的“色彩”排列是如此的严整,以至于让当代的世人惊叹中国古人在色彩学方面的探究,何以早已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
三色的探究不仅仅是色彩本身,它是上古中国人对于自身天人关系的一种认同。
《论语·八佾》载哀公问“社”,宰我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显然,夏为青,商为白,周为红。三代社木所追求的色彩,与现今的中国画如此相同,简直是如出一辙。《礼记·檀弓上》则说得更明白:“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牲用�”。按照《礼记》的此种说法,夏朝尚黑,商朝尚白,周朝尚赤。在现有文献中,华夏国、华胥国和华阳国等三华国在色彩的追求恰恰是与三代对应着的:
华胥国——月——白色——商朝
华夏国——(黎)日+月=明(天)——黑色——夏朝
华阳国——日——红色——周朝
三华国以及三代的色彩追求,是李泽厚《美的历程》以及他与刘纲纪二位先生合著《中国美学史》第一卷未及论述的。但这些色彩的运用,在中国画这里却一直在延续着。放眼看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美学史上,有中国画家有如此严整的色彩运用。
也正是因为此三色的搭配,所以中国的国画与西方的油画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国画一定要“空”,而西方的油画则要“满”。
其次,国画是“水”画而油画是“油”画,中国的国画是离不开“水”的。墨与纸张都是“木”,一个是木质的产品,一个是木质的灵魂。说中国画所展现的乃是“水木清华”,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
第三,国画是散点透视而油画是定点透视。散点透视是“神游”视角,定点透视是一人立定所见。前者是上海世博会展出的《清明上河图》,后者是文艺复兴式透视,巴黎卢浮宫收藏的格罗1796年所作油画《拿破仑在阿尔柯桥上》以及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收藏热拉尔1805年所作油画《雷加米埃夫人》,都是比较典型的定点透视的绘画作品。说的明白一点,达·芬奇等文艺复兴三杰的作品,在透视方面与现今的照相十分相似,而《清明上河图》则是类似现今在直升飞机上的航拍所得。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一直强调艺术必须讲究超越,柏拉图自己强调的“美的理式”甚至要超越具体的存在,但是在时间方面的超越,张择端比达·芬奇的步子显然大得多。
最后,国画的画面上,绝大多数是“人在景中”,而油画中则是让人压倒了景物。
如此这些的方面,使得唐、宋、元、明、清的历代文人都十分醉心于中国画,中国的老百姓也因为这是中国的画而对其钟爱有加。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中国人又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后人,他们的审美趣味不是任何外力可以改变的。即使是齐白石,当他在《白石老人自传》中说“(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也不过是让印章上的红色也在画面上出现而已。陈师曾、徐悲鸿之所以看重这位来自山野的老农夫,是因为他们都天才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脉动。
我看尹沧海教授的画面,其中也有别的色彩,就悄悄地问他。尹沧海马上回答:“用色以补墨之不足”。
好一个“以补墨之不足”!白石老人的绘画,说到底,也还是墨色、白色、红色的三色舞曲。
墨才是国画的灵魂所在,白色的质地是为了突出这种墨色,其他的色彩是为了烘托与映衬这种墨色。难怪我的许多研究美学的朋友评论说,尹沧海教授的绘画中充满了一种文人的情调与追求。他是画家,也是高等学府中的教授,他的绘画理论与其画作一样出色。
宽大的画室里面,墨色在随着画家的手腕而延展,我嗅了嗅,空气中有隐隐的墨香。
我对于眼前的这种墨色与墨香有一种眷恋,就如同绝大多数学习中文的人一样。因为这是线装书的书卷透出的味道,是线装书卷中没有色彩的色彩。墨色非色,就如同公孙龙“白马非马”命题一样的玄妙。它是九天玄女之“玄”,是天后宫里的“黑面妈祖”之林默娘之“默”,它是天之色彩,时而清澈无比,时而变幻无穷。我国历史上的信奉对象也算是丰富多彩,但是对于上天的信奉,却是一以贯之的。河北省保定市“直隶总督府”内,至今还有宋人黄庭坚手书的《御制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餍,上天难欺”。
尹沧海教授的《相约水云间》画面上的鱼已经画好了,荷叶、水草以及菡萏都在画面上出现了,巨大的画幅将传统的中国画的景致推出来,栩栩如生。这就是抒情,是中国人历朝历代都极为推崇的诗情画意。其中没有叙事以及西方学者所推崇的“叙事学”内部所存在的二元对立关系。自从白行简(776-826)《李娃传》当中才隐约出现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中国文人以及中国老百姓看得到但是不愿意欣赏的。除了专业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员,白行简之名在中国大众心目中并不重要,他与乃兄白居易之间的知名度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叙述的最终极致是矛盾,其内在的结构是冲突,甚至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极力讲述的剧烈的、白热化的冲突。叙述的矛盾起源,无论如何也与位于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古希腊、古罗马人生活的自然条件脱不了干系。我们可以把这种被利奥塔德(J.F.Lyotard)尖锐批判的西方“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归纳为如下的“聊斋”模式:
1.“一个书生去赶考”
2.“走到半路被雨浇”
3.“迫不得已进破庙“
4.“又饥又寒睡不着”
5.“忽听窗外有人笑”
6.“窈窕淑女已来到”
7.“书生尸骨抛荒郊”
在这个模式中,雨水与书生构成了矛盾,人与自然所形成的是对立关系。“破庙”与人构成的也是如此关系。即使是书生自己的身体状态,也与他为难。他又饥又寒。此时进来的人虽然貌若天仙,又带来了食物与衣服,但是,她是他的对立面,因为她是妖精。西方的文艺作品里,表现类似对立的不可胜数。不仅有人与自然对立的《鲁滨逊漂流记》,有灵魂与思想对立的歌德的《浮士德》,甚至还有英雄与自己之间的搏斗。我们可以看一看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胜利者》:
在翡冷翠的国家美术馆中,有一座为米开朗琪罗称为《胜利者》的白石雕像。这是一个裸露的青年,生成美丽的躯体,低低的额上垂覆着鬈曲的头发。昂昂地站着,他的膝盖踞曲在一个胡髭满面的囚人的背上。囚人蜷曲着,头伸向前面,如一匹牛。可是胜利者并不注视他。即在他的拳头将要击下去的一刹那,他停住了,满是沉郁之感的嘴巴和犹豫的目光转向别处去了,手臂折转去向着肩头:身子往后仰着;他不再要胜利,胜利使他厌恶。他已经征服了,但亦被征服了。
这是罗曼·罗兰著作《名人传》中《米开朗基罗传》中的著名片段,米开朗琪罗所造就的这位战胜者,被自己的胜利战胜了,“他”的成就成了“他”的对立面,人与自然构成矛盾还不够,人与他人构成矛盾还不够,人与其自身又构成了一种矛盾。这就是西方经典的欣赏趣味。
我看到的眼前的绘画是与这些叙事完全相反的一种作品。画面上是一种和谐,鱼与看不见的极为清澈的水是和谐的,因为有了鱼,才显出了水,或者说是暗示了水;因为荷花与荷叶,水与鱼之间的关系更加显得自然。事实上,从明代文人谢榛《四溟诗话》里激赏的两句诗“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古代汉语诗学根本就不愿意强化对立关系。那么,上述这10个字作为文本,是否存在着人物与环境的对立、人物与其他人物的对立、人物与自己的对立呢?可以肯定地说,不存在。“雨”的出现才使“黄叶”具备了声音,才显示出了黄叶。因为黄叶的滴答声,才更突出了“雨。”它们之间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同样道理,“雨”与“灯”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像雨与赶考的书生一样的对立关系,而是“打成一片”(布莱克语)的关系。它们共同营造着一种气氛,一个意境。
就在《相约水云间》的诗情画意已经基本营造出来之时,画家手握大笔,从巨大的画面右上方向着左下方迅速地拉出一条粗重的墨线,在场的几位观赏者都不住叫好。我也对着这一条曲线出神,觉得它是那么优美,那么神奇,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国画的神奇魅力,感觉这就是宋朝著名画家兼绘画理论家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中所说的“景外意,意外妙”。
《相约水云间》画成了,我的视线还是紧盯着那一条美妙的曲线。北大彭锋教授2009年在本校出版社出版《回归》一书,其第二章《审美对象是何物?》追溯了朱光潜“物甲”、“物乙”之说。朱先生经常把“物本身”与“感觉素材”称为“物甲”,把“物的形象”或“艺术品”称为“物乙”。彭锋教授认为,朱先生所说的“物乙”其实就相当于审美对象,但西方的哲学家萨特不这么认为。萨特认为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存在于心灵中的“皮埃尔的像”(image of Pierre),我们只有“对被像想着的皮埃尔的意识”之类。萨特将所有不跟对象直接遭遇的意识方式称为“像想”(imaging)。我不知道萨特先生见到中国画时,是否还会坚持其自己的哲学见解。《相约水云间》是标准的“物乙”,画面上这一条漂亮的曲线不是什么“像想”,因为即使拼命地“想”,它也根本不是什么“像”。它是画家以及欣赏者在画面的景致中发现的“意”,并将其升华为一种不可言说的“妙”。
在我看来,这一条优美的曲线是这幅画的灵魂,它用墨色将画面上的其他颜色统一起来,三色彼此映衬又有主次。这一条优美的曲线也是这幅画的主旨,它将画面上的诸多物象勾连起来,彼此映照又彼此烘托。曲线自身的毫不犹豫、势如破竹又毫不武断、毫无霸道之气,则是“天行健”古训带给画家的自信的具体显现。这也是中华文化的自信,我以为。
2012年11月
作者简介:
刘顺利,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市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韩国“中国语文论译学会”海外理事。文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美学与文学理论。学术成果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生理美学》,《美育学概论》,《美学原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