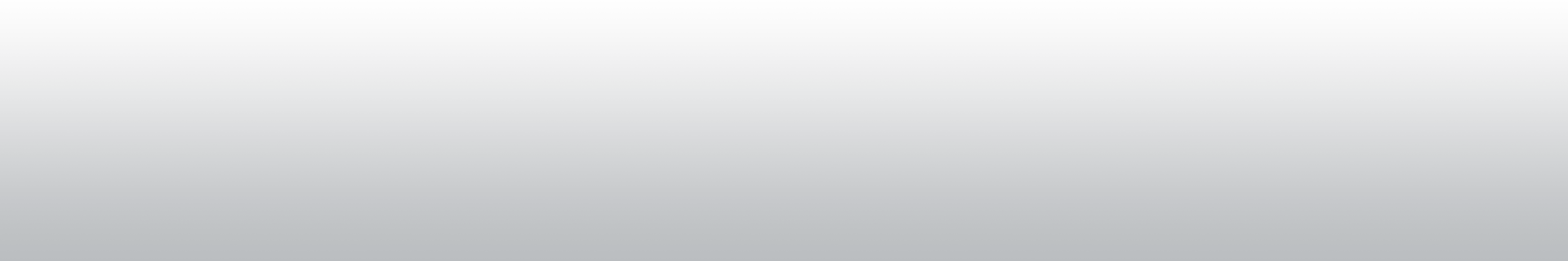王志耕
我跟沧海交往多年。我虽然不懂画论,但艺同此理,我想我从画如其人的角度来谈谈,或者用我们文艺理论的行话说,从“作者”的角度来看看沧海的画的审美价值。当然,这其中也涉及到好的艺术作品的生成机制的问题,就是说,一种好的艺术是如何产生的,其审美的效果应当如何。
看到沧海的画我就想到这个人,而想到这个人,再看他的画就会觉得两者其实是统一的,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看上去很神秘,其实并不是无法解释的。当然,作为从事绘画创作的人,不论是画家还是学生,却未必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或者也可以说,他最好不明白这个道理。过去有一次跟艺术系的老师和同学们座谈,我就说,搞艺术创作的人最好不懂理论,因为理论思维与创作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你过于理性,艺术的生命冲力就减弱了。法国的哲学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柏格森就认为,一个人过于理性,他的生命冲力就会被压抑,生命本身的价值就打折扣了;因此,人应当保持某种直觉状态,来克服人在理性状态的游移、冷漠,从而获得生命的豪迈向上的精神。无独有偶,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过类似的话。看来这不是偶然的,大家都以为哲学家都是冷冰冰的思想者,像康德那样,一辈子不结婚、足不出户,闷着头子在屋里思考的人。其实,哲学家也可以像罗素这样,离了婚再结婚,甚至主张同性恋合法,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甚至坐监狱。他就说:“理智是人类的不幸。”所以,人类应当恢复“直觉”,像蚂蚁和蜜蜂那样,因为“直觉”状态是无私的,在这种状态,人就具有把自我和无限的宇宙统一起来的可能,而人在理智状态呢,他思考的对象就变成无机的了,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所以他就说:“理智的特征就是天生没有能力理解生命。”说到这儿,就使我想到了沧海的个性。
我觉得,沧海的个性有三个方面是与他的绘画有直接联系的。第一是率真,有时即使是在正规的场合,他的行事也像孩子一样,无所顾忌,率性而为;第二是激烈与平静相结合,这一点在他身上看似矛盾,但其实是统一的,他有时很热烈,性之所致,既可以怒火三丈,也可以兴高采烈,但有的时候他又很安静,可以一夜一夜地琢磨他的画,更有的时候躲到深山古寺,远离尘嚣几天、几十天。所以,这两点在他它身上竟然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看他,大多数时候表面看着激烈,其实他是个内心很静的人。有时他看上去整天都在忙着上课、画画、搞展览,甚至为了做成一件事去托人情、拉关系,但是他心里是干净的,坦然,无愧。第三点是,他还有机巧的一面,大家看他现在每天头剃得光光的,面相庄严,看上去像个拙于行、讷于言的老和尚,其实他内心深处有很机巧的一面,也许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从他的偶然一笑中看出他的巧智。大家不要小看这种巧智,没有这一点,要想做艺术这一行是万万不行的。
率真是一种天性,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种个性,虽然一般而言小孩子都有率真的一面,但到了成人阶段,仍然能够保持这种率真的人慢慢就越来越少。社会这个东西就是个机器,是一个磨光机,随着你不断地长大,你的那种小孩子气就越来越少,就被这个磨光机磨平了,变得越来越没趣,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喜欢小孩子的原因。你自己身上的那种童趣没有了,实际上你又非常怀念这种童趣,所以就只能在孩子身上去找,去寻找你已经失去的那种感觉。但成功的艺术家,他们的身上却会把这种小孩子才有的率真一直保持下来。沧海就是。那么率真跟艺术创作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为什么只有保持率真的品格才能创造出好的艺术作品来呢?这得从人理解和接触世界的方式来谈。具有率真个性的人,他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一般的、理智思维占主导的人不同。实际上我们常人理解解世界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个屏障,这个屏障,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把它叫做“符号”。其实,人类自从进入到现代思维阶段之后,就失去了直接把握世界的能力,或者说靠直觉来把握世界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当你看一个事物的时候,你脑子里首先出现的是一连串的语言符号,而不仅是一个“感觉”,一个形象,这是由现代思维特性所决定的。当然,在原始思维阶段是不同的,那个时候人还没有成熟的语言符号来表达意义,所以那个时候人理解事物是靠整体性把握,用的是“接触性思维”。卡西尔说这也是一种语言,不过是一种“隐喻”的语言,它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感性体验。但后来人有了系统的符号语言,就把这种体验给规范住了,这一规范可不得了,结果就把人和世界隔离了开来,此后,人就生活在了一个“符号的宇宙”之中,他不能再直接面对实在,他被包围在了一个符号的牢笼之中,如果不通过这些符号,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所以,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也许卡西尔有点夸大其词了,但它说明了一个道理,现代人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实际上远离了那个真实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虽然可以创造文化,但如果你想创造艺术品,那么对不起,这个艺术品可能是十分理性的东西,是由理性符号编织起来的,不但谈不上艺术的真实,甚至远不如真实的实在更丰富。那这个艺术品还不如不要。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人之所以要创造艺术品,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要还原那个本来丰富的世界,但因为有了符号的屏障,这个世界就远离了我们。因此,要再现这个世界,就要靠那些还保留着某些原始思维特性的人去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再现,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艺术创造活动。所以,那个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法国人斯特劳斯也说过,艺术是“野性思维的国立公园”,这种思维就是那种没有被社会“驯化”的孩子似的思维。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就是说,只有保持率真的个性,才具备这种思维能力,并创造出好的艺术作品来。从沧海的画中,你可以看出,无论他用的是哪种绘画的手法,其实都显示出一种率性而为的特点,而恰恰就是这种特点,却包含了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刚才我说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热烈与平静的有机结合。这个问题涉及到艺术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就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而言,艺术的功能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把我们从已经自动化的生活中抽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只要大家思考一下人为什么会去从事艺术创造,也许就容易明白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慢慢被消磨,你就失去了对生活的新鲜的感受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习惯动作,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周而复始地重复过着一种日子会是什么感觉,那就是麻木了。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把这个叫做“自动化”,就是说,你天天如此,都做一样的事,你对你做的事就没有感觉了。托尔斯泰曾经写过一篇日记,说他每天都天擦桌子、沙发,可有一天他擦完以后,回头想,哎,这个沙发我到底擦了没有?刚刚做的事,他就忘掉了。这个道理说明什么?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对我们日常所过的生活已经自动化,习惯了。人在这样生活中就失去了激情,所以什克洛夫斯基就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艺术家具有特殊的、把生活“陌生化”的能力,能把人从自动化状态调整到热烈化状态,使你对生活重新燃起热情。我看沧海的画就有这样的感受。我不懂画法术语,人们说他是大写意,但我看他的画,会感受到他的激情把我从日常自动化的生活中拉出来了,拉到一个重新感受生活、对生活有新奇感、有激情的状态。你会觉得,你天天都看山,看水,看树,看花,但你都没注意到,原来这些自然界的东西还具有这么一种“非自然”的、变形的、充满了张力的形态。这也就是说,你一个艺术家,如果你没有热烈的情绪,你看这些自然界的东西的时候你都是冷漠的,不动情的,没反应的,那你怎么可能让你笔下的东西能够打动别人呢?你只有以热烈的情绪去面对事物,你对它充满了激情,你才能把这种热情传达给别人。刘勰说:“方其�翰,气倍辞前;既乎篇成,半折心始。”意思是,就算你刚拿起笔的时候充满了激情,但一旦文章写完了,你再一看,刚开始的时候那种激情只剩了一半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超乎常人的热烈的、甚至是看上去有点疯狂的情感,你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又跟日常事物差不多了,同样是死的,没有热情的,也就不会打动人。当然,艺术不能总是让人热烈,其实,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逃离和否定的功能,什么意思呢?人在生活中不仅是一个“自动化”的问题,还有一个厌倦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对现实生活永远是不满的,而人为什么会进行创作,就是想在现实不满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再造一个世界,让我们有一个存身之地。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有觉得很烦的时候,这是海德格尔用的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个普遍的概念:人的存在就是“烦”。虽然海德格尔说的“烦”和我们日常所说的麻烦有不同,但大致意思可以相通。你烦,是因为找不到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感受,就是一种被“抛到边缘”的感觉,这时候你就会去寻找那个真实的自我,要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否则严重了就是彻底否定自我、自我消失。那么,在现实这堵高墙面前,你往哪里去找那个真实的自我?有一个方式,就是艺术品,你去创造也好,欣赏也好,总之,艺术作品会给你营造一个远离“烦”的世界,一个平静的、理想的空间,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一个澄明、空寂的状态。其实这个功能和佛教所讲的“空”的有点相似。佛教为什么讲“四大皆空”,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要你逃脱物质的缺乏、争夺给你造成的欲念、烦恼。但佛教那个“空”是虚的,你看不到,要靠自己去参悟。而艺术的感受是直接的,你读了一首好诗,面对一幅空灵的画,就可以直接进入那个“虚空”的世界,从而暂时地抛开了尘世的各种烦累。有人说沧海的画受了他接受的佛学思想的影响,我想这是一方面。其实在我看来,空静和超脱也是一种天性,有时修炼出来的东西很难与天性中本来就有的东西相媲美。我是觉得,沧海的画在热烈与空静之间有一个平衡,他的热烈把你从淡漠的生活中拉出来,然后又以他的高远、缥缈、平白,把你带到一个平静的、舒适的世界。能造成这种感觉大概是中国传统画的优长,我看凡高的时候就找不到这种感觉,他太热烈了,因为他本人的个性就是疯狂的。这也是西方人的普遍特点。所以,我更喜欢沧海的画里面的这种平静,找到这种状态,就觉得生活很澹然,名利困扰都消解了。
我说第三点,就是机巧。刚才说了,沧海这个人看上去很“粗放”,其实也未必。他是有直率的一面,但并不是说他的画就是胡乱画出来的,想怎样就怎样。其实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是要有一个“度”的。说起来,这个“度”,我还是认为它是一种天赋。也就是说,所谓“机巧”,固然有训练的成分,要掌握技巧、要熟能生巧。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天分,你再“熟”,也生不出“巧”来。如果仅仅强调训练,那么,这个世界上用苦功的人太多太多了,可为什么真有成就的人那么少?这就是说,这个“机巧”首先要在你的天分里存在。而这个东西是成就一个艺术家的专业才能。有率真个性的人也不少,也有人既热烈又平静,也有人具备了很好的艺术感受能力,甚至有的人见花落泪,临水生情,可是他们却还是成不了艺术家。为什么?就是没有天生的这种“机巧”。这个东西在艺术理论中叫做“符号化能力”。钟嵘的《诗品序》有这样的话:“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就是说,你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境况,不表达出来你就难受,那么怎么表达呢?一般的人就是哭哭笑笑而已,但艺术家就不同了,他会通过写诗、唱歌、跳舞,当然还有绘画,来表达。那为什么艺术家能,而普通人不能呢?这里面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就是从体验向符号的转化。刘勰说有了情感要表达,这时候先要“志思蓄愤”,就是把自己的情感加以积蓄、培养,然后再“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最后表达为一种艺术的“形式”。美国心理学家阿恩海姆说:“视觉不是对元素的机械复制,而是对有意义的整体结构式样的把握。”听上去比较绕口,其实就是说,你看到了东西,但不能把这个东西原封不动地画出来,如果要画出来,就要画出这个东西所蕴含的更丰富的内容。比如沧海的本科毕业作品《高原》,你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黄土高原,看到的可能就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但当它转移到一个艺术家的画作上时,它就具有了雄浑的气派,有了力量,有了沉重。这就是它经过了艺术的符号化的处理,成了一个在一个具体事物中体现整体意义的东西。沧海自己也说:“有法与无法对于一个写意画家来说,是取决于创作时的创作心理状态和技术熟练程度造成的心手相应的境界。开合、疏密、虚实,章法韵致等因素因特定需要而定。切不可把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自由状态看成是胡涂乱抹,因为创作者的所谓‘自由’也是有度的,其点画披离的‘自由’创作形态是在其‘时见缺落’中显示出文人写意画家的高华之内质。”(《关于笔墨的有法无法之论》)这里不妨给大家读一段苏珊·朗格的话:“当我们以‘画家的眼光’看待自然,以诗人的思维对待实际的感受,在鸟雀欢舞的动作中发现舞蹈的主题时——就是说,任何美丽的事物激励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地感觉到情感的形式。用这种方法感知的对象具有一座庙宇或一块纺织物所展现的相同的幻觉神韵,从物理意义上说,它与鸟雀、山岳是同样真实的。这就是艺术家们之所以能从自然中吸取一个又一个取之不尽的题材的原因。但是,自然客体只有在发现了客体形式的艺术想象中才能成为有表现力的东西。一件艺术品,在本质上就具有表现力,创造艺术品就是为了摄取和表现感知形式——生命和情感、活动、遭遇和个性的形式。”这个话要我解释就是说,你只有感受,只有“思”,只有“愤”是远远不够的,你要有一种天赋,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事物时,能够把握到这个事物的特殊“形式”,它包括了你整个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最后才能转化成真正的艺术的“形式”。
我最后要说的话就是,沧海有这个天分,他有这种机巧,从他的画中能感受到他的生命体验,他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一眼看去,他的气魄、情感,整个地都展现在面前了,但是仔细看,里面还有思考,有设置,有排列,有讲究。比如说,这只鸟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山坳之间加一个人的影子,或加一幢房子的影子,等等。你只有沉下心来,最后才会明白,它为什么会给你震撼,让你激动,让你出神,是因为,它既有艺术家的超乎寻常的情感,也蕴含了先天秉赋的艺术形式化的能力。
作者简介:
王志耕,男,1959年生于河北任丘。文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兼职教授。1982年3月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5-1988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文学专业,师从王智量教授,获硕士学位。后任教于河北师范学院(1996年合并为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1993年分别以国家教委公派访问学者和校际交流访问学者身份于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师范学院和伏尔加格勒师范大学进行访学。1997-2000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师从程正民教授,获博士学位。2001年7月受聘于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