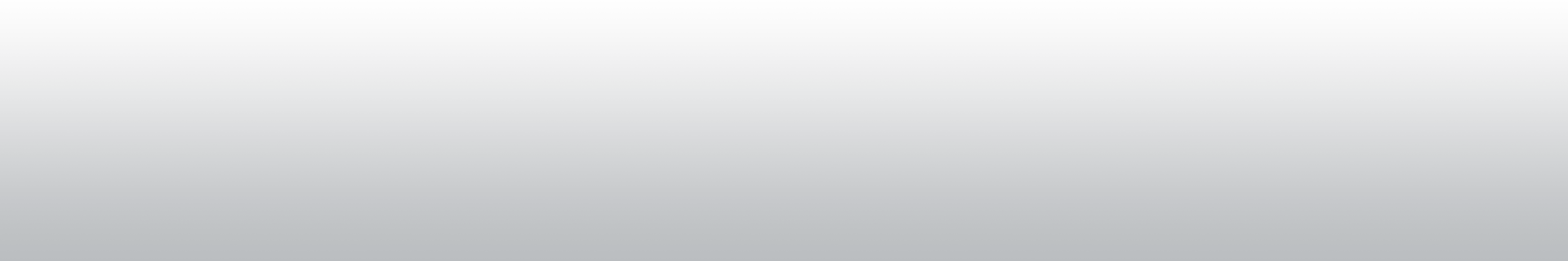南开大学哲学院 薛富兴
挚友沧海兄又要举办画展了,心里真为他感到高兴。本人虽然也喜欢观画,但毕竟是个外行,有的只是些粗浅感受,难以用专业的精准语言正确地表达沧海兄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在今天这个令人喜悦的日子,且写下些零散的审美感受,以表达对沧海兄的祝贺。
一
沧海兄首先是个很勤奋的画家。自其1995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沧海小品”展览起,几乎每年都有新作汇报展性质的个人画展。这种持续性极强的个展,实在要以艺术家日积月累的辛苦劳作为前提。各式展览上所展出的作品,其实只是沧海兄日常劳动成果的一部分,更多的作品则为其身边的朋友们所收藏,或者静静地躺在其画室的某个角落。我不止一次参观过沧海兄作画。一幅作品最后被悬挂在美术馆墙上,参观者往往会叹赞其精致、美艳;可是,只有当我们现场了解了艺术家的作画过程时,才会真切体会到:其实,每一件精神产品的创造,对其创造者来说首先是一个平凡、辛苦,甚至琐碎的劳作过程;一件有着深刻精神内涵的艺术品的创造,对画家来说甚至首先是一桩体力活儿。沧海兄每每喜欢弄大幅作品,这便实实在在地苦了他自己。为了筹备现在这个展览,沧海兄在今年夏天可谓苦战于大禅堂。看他整天在画室挥汗如雨的样子,我心中不禁起大疑虑:谁说艺术创造是一种诗意的生活,谁说只要有诗情与妙思,便可成为一个艺术家?不,从沧海兄的辛勤劳作过程中我体会到:其实,做一个艺术家与当一个农夫无异,最要紧的就是诚实劳动,要有一种不怕苦、不嫌累的精神,在劳动态度上首先要憨厚、勤勉。沧海兄在许多画作上题有“大醉而写之”之类语,每让观者神往于他酒神式诗意与才华。但是,我在观其作画过程中更多地体会到的,是沧海兄作为一个画家之苦辛。每个大构思、大布局,都是画家给自己下了个套:需要他用心研究每一个角落到底该如何处理。依国画“计白当黑”理念,那些留白处千万不能理解为画家在偷懒,而是其精思妙想之后对虚实辩证法的尊重与妙用;至于那些需要他用笔墨悉心填补的空间,画家则往往再三再四地去勾勒或点染。沧海兄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不想在任何一个作品,甚至每一作品的任何一个部位有所疏漏,有所遗憾。这便苦了他自己。当他认真修补画面细节时,更像一个绣娘,与其魁梧身材形成巨大反差。有幸得到沧海兄画作的朋友们,请好生善待这些作品,因为画家于其每件作品、每个画面上的每个细节,都付出了自己的体力、情思与才华,都付出了他的诚实劳动。人生是有限的,艺术家所能创造的艺术品也有限。只有认真尊重艺术家诚实劳动的人,方可作艺术家的挚友、知音。
二
在这个全球化、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主潮的时代,沧海兄则是一个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忠实守护者,是一个乐于在当代社会发扬传统审美趣味,坚守写意理念的画家。
在当代中国画家中,沧海兄以其大写意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赢得广泛声誉。
依理,绘画当是典型的再现性艺术,但是,在悠久、发达,更为深厚的诗歌抒情传统与早熟的书法艺理双重熏染下,中国古代绘画自中晚唐即自觉地走上主观性表达,至少是再现与表现相融合的独特道路。至宋,人文写意画成为中国古典绘画主流面目、主导观念。到二十世纪,当我们可以直面随“西学东渐”大潮而来的西方写实绘画时,便更加直观地意识到本民族传统绘画的独特个性,这便是写意画所集中承载的绘画理念——以笔塑型,以墨写意,意象融彻,物我浑成。自20世纪前期西画涌入,现代中国画坛已然不再是国画一枝秀独之局。相反,在西方思想、文化观念的全方位冲击下,传统绘画技法、观念和趣味受到很大挑战,以至于20世纪画坛不只一次出现过关于中国传统绘画观念合法性的讨论,也出现过“笔墨等于零”的极端性言论。
沧海兄虽然出道较晚,上世纪末才在画坛露面,但是,就他的绘画领域、对象、技术与审美趣味而言,典型地属于传统一路。而且,考察他有关绘画的言论会意识到:他对于自己艺术理念的选择是高度自觉的,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绘画理念是着意继承,并很愉快地践行之。正因如此,他才如此挚爱于写意画,并在此领域取得突出成就。
写意精神首先便是自觉、突出的艺术家自我表现精神,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以中国绘画所特有的笔墨语汇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感,这便是写意画核心理念。从接受角度讲,写意画的独特审美魅力正在其坦诚率直,那是画家与欣赏者零距离的心灵交流,画家直呈其心,观者悉心倾听。直呈本心正写意画之独到本色。直以笔墨迹拟造化,浓淡疏密总是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游戏营造出一个个有情世界,此正沧海兄画作之所为。故而沧海兄之写意画作总有一种扑面而来,直接摄引观者的直观效果。或花鸟,或山水,或人物,总能别造一境,渲染气氛,引人足目,引人流连。观者乐意在那尺幅上的小小世界适性徜徉,做广阔无垠之逍遥游,为之感动,为之出神,为之宁静,为之旷远,岂不妙哉?在以墨言情方面,有一组作品似可为代表。《谁持墨练当空舞》似可直接体验为墨之舞,墨之诗;《终南山月下写生》以迷离、漂移之笔墨为月光下的终南山留影写照,最终营造出一幅若有若无的朦胧幻影;《祗园霜晨》那峭拨的疏枝与横向晕染、化开的墨云相交织,形成一个清冷而狂放,浓烈又轻盈的奇异世界。《天华峰月光下写生》二幅亦然。其造型之笔极为简疏,着意于在墨的浓淡变化间创造特殊氛围,《之一》疏朗,《之二》浓烈。《祗园寺后山意象》几乎纯以墨造型,那氤氲的墨团似正聚成山的轮廓,但我更愿将它想象为一簇在宇宙间偶然聚合的阵云。画家在左下方随意涂出的一小块暖色,正反衬出这整个世界的寂冷。如果说黑白世界乃沧海兄绘画之主体,有时他也乐意呈现众色相。《祗园寺秋深》虽然在墨色之外的其它暖色应用上极为克制,但是,那率意间淋下的点点滴滴色斑,却与粗墨树枝相对照、呼应,构成一个寒意与温润相交融的世界。对写意画这种特殊的绘画艺术而言,墨似为第一语汇,第一直觉,无论对画家与观者均如此。能呈现写意画强烈抒情性者,正是画面上由墨之浓淡变换交织所形成的扑面而来的表现性氛围。在此意义上,何为写意画?墨戏、墨艺、墨诗、墨道之谓也。沧海兄似正长于此。其《迎风归去》,乃师范曾先生题云“尹君写意,墨韵最佳,并世不可多见”,当正指此。
沦海兄每每反对以西释中,怕引起对国画精神的不必要误解;但是如果我们不局限于中西绘画表现的具体内涵差异,而着眼于其主观表现性之核心理念,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写意画所营造的自我表现之境,其内在气质与方向,似正可与现代西方艺术强烈、自觉的主观表现精神相通。某种意义上说,沧海兄用纯正传统技法、材料所描绘的境界与现代西方印象派、表现派绘画所营之境,内在气质上极为相似,也有大致相当的欣赏效果。西方绘画长期坚持写实传统,到二十世纪始有反其道而行之者;但是,中国古代绘画则很早即有非常自觉的自我表达理念,在以造型手段表达艺术家主观世界,即表现性上,以写意画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绘画其实是早熟的。传统的中国绘画形式、理念完全有能力与西方现代艺术精神相沟通。
如果说以墨造型、以墨创氛,以墨写意,在墨的浓淡变化间模拟造化,揭诸人心,是写意画主要手段,其实,作为古典艺术形式,写意画在大部分情形下并未走极端,没有发展到纯墨戏,没有走到有墨无笔,有意无形的境地,而是走了一条中道,一条兼顾笔墨的道路,这也许正是中国写意画与西方现代表现艺术之重要区别。主要原因似有二:一是写意画作为传统绘画,仍正视色彩、线条之造型基本功能,因而没有像现代西方艺术家那样,将绘画之再现功能,将具象之形完全逐出画面,以为“全不似则近乎欺世”。其二,以写意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绘画,又在书法艺术的巨大影响下成长,因此,书法的因素——笔,具体地,以书法之笔描线塑形,以书法之粗细、急缓、轻重自觉变化之线条或造型,或写意,乃写意画又一基本理念,乃至在画界树立起有墨无笔不成画,近于俗的理念。因此,笔的因素,具体地,由笔而来的书法性线条,讲究粗细、缓急、轻重、疏密变化之线条,最终构成写意画核心语汇之一。画面中有无笔痕,线条处理得如何,是否自如、纯熟,是否有变化,是否有力度,等等,又成为同行评价画作、画家艺术成就的重要内容。凡有墨无笔,或巧于用墨,而拙于用笔者,均不会得到很高评价,会被认为是不完善的绘画,是无功力、缺素养的绘画。
沧海兄作为传统绘画理念的忠实继承者,他在笔的方面也很自觉。他既有抒情意味十分突出,以墨趣引人的作品,也有平实典雅,笔墨相济的作品,此可以《凌波独叶红》、《藕花扶梦过西冷》、《万里秋风自在天》和《应解自呼名》等为例。这些作品兼具再现趣味与抒情趣味。如果说画家在这些作品中对墨的挥酒自如集中体现其表现趣味与才华;他对树木花草、飞鸟虫鱼的精心描摹则体现了艺术家对自然对象之忠实与尊重,其逼真传神的再现效果便体现了画家扎实的造型功力,体现了其画笔之精准与纯熟。
沧海兄虽以写意画知名;但他仍有一批足以体现其写物功力的作品,主要花鸟与人物,诸如《虎啸千山》、《秋风清》、《南园春色佳》、《春消息》、《迎春图》、《修羽临风翠欲飞》、《闲卧蕉荫雪皤皤》等。艺术家之主导意趣在于写意;但他同时也乐于以工笔细刻万物,追摹造化,因为他意识到这也是艺术家超越自我,苦练内功,厚础强基的重要手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以典型、完善的国画观念看,凡能工笔者方善写意,惟知墨趣墨戏便不足以成就一个高素养的写意画家。
写意只是其自我表现之大致范围。更准确地说,沧海兄每喜弄“大写意”,非如此,似不足以逞其才,快其意,浇胸中块垒,展自家面目。何谓“大”?盖谓大布局,大构图,大挥洒,大涂抹之类。前面提及其墨诗墨舞已足见性情。墨相外,他又多以构图之精巧、布局之宏阔、物象之精微、寓意之深厚而取胜者,诸如《东风吹雨过春山》、《清风送和鸣》、《晚风史行舟》、《若耶秋》等。且观其《宇宙苍茫秋气高》。此作以浓墨涂雄鹰之巨翅、太空之层云,以劲笔写鹰之电目、利爪,上留巨白,下映以疏畅之劲草。布局宏阔,气象萧森,现苍茫秋境,颂劲健枭雄。展卷细品,诚能快人目,爽人神者也。
与其大留白、大布局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其简约之勾勒、精微之造型。简笔、浓墨、大留白三者聚为一体,使画面内部充满张力,每引观者深思细赏。此类作品有《识勾否》、《梅林春早》、《鱼戏莲叶东》、《细雨鱼儿出》和《远离颠倒梦想》等。极度的夸张与简约需要巧思与智慧。也许正因如此,乃师范曾先生喜题之以“有八大之意”。一言之,所谓大写意者,能以笔墨营构大境界,能拓展观者胸襟之谓也。大写意画似音乐中之交响宏构,每令欣赏者畅快淋漓。
沧海兄之写意画充满传统人文意趣,可谓之当代文人画。论其纵情写意,每及于酒。他每喜在酒意微醺状态下挥毫泼墨,醉后又常有妙作,故而题画之辞多及于“醉”,此正中国艺术传统中之妙谈,李白、张旭每能如此。沧海兄持自然主义艺术观,他着意强调画家要在自然无碍,非思非虑的状态下,随笔势墨趣之自然而作画,不要有过多的理性思考与掌控成分。如果画家在创作过程中过分强调理性与事先规划,实际效果往往不能如意,甚至会适得其反。酒精因素参与下作画,正是这种顺性自然创作理念的极端形态,且看他的相关文字:
一笔既下,一笔已应手而起,如此一笔,二笔,三笔乃至于百笔不穷,画面造型之取舍、笔墨之变化,已非先前所预想,自然而然笔行而墨随,合于理法而奇趣自生。
这是沧海兄的见解,其实也是中国古代艺术之传统理念,无论道家、佛家,都强调心灵的自由、空灵、虚静状态。惟在此状态下方可产生文化精品。理性意志的过分介入,有时会变成一种干扰。
写意画发展到宋代,有了一个新名字——“士人画”,后称为文人画。文人画不只是抒情性艺术,也是一种综合艺术。其中,文学的介入十分重要。其内在的表现是诗歌意象、趣味成为绘画的主体观念,外在的表现形式便是画家在构图中会预留出一定空间,以便画成后再作文学性题跋。题跋语又以诗句居多。这些简约的诗性文字对画面形象与意境往往有概括、强调之效。更重要者,从接受效果看,这些题诗之诗意往往与会画面上由笔墨所构形象相互补充、融合,最终形成更为绵密、完善的审美意象。于是,诗歌趣味与绘画趣味相互促进,实现了双赢。中国古代士人在知识、技能结构上是诗、书、画兼修,文人画这种集文学、绘画、书法,印章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正可充分、完善地体现文人的文化修养,所以,宋后文人画便取得稳固的地位。现代艺术家若想继承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也就必须同时自觉地继承传统文人诗、书、画兼修的综合型文化知识结构,完善自己的艺术修养。作为一个国画家,沧海兄在继承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方面,也很自觉。一幅作品画毕,他每每喜欢题一二诗句以概括之,揭示之。这些诗句所蕴含的意境或清新,或典雅,或深邃,或玄远,或古淡,或宁静,对画面总有提升、丰富、拓展、深化之效。对于诗歌与绘画的融合双赢之效,古人早有体会,固有诗画一律之论。沧海兄于此可谓深契。
在当代社会传承与发扬古典文化精神,对于一个国画家而言,除了对笔墨精神的谨守与精熟外,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之了解,以至挚爱,也很重要。毕竟,诗歌乃中国古代艺术之重镇;毕竟,古代画家有诗画双修之功;毕竟,诗歌对中国绘画主题、内涵与风格均有深刻影响。就写意画而言,诗题、诗性与诗趣,似乎已成为绘画意境之重要组成部分,一幅写意画若少了诗兴与诗意,便会魅力顿减,至少是单薄、不完善的,这便是诗歌影响下的写意画审美趣味。观沦海兄之画作,以诗命名者可谓泰半,诸如“斜日寒林点暮鸦”、“谁持墨练当空舞”、“碧牵文藻舞轻柔”及 “四月江南橘正熟”等,可谓径将诗境为画意之例。这便使欣赏者在观画之余,不自觉地浸淫于古典诗词境界,得到诗歌语言、情趣的熏陶,同时也培养了当代中国绘画欣赏者对自身诗歌传统的心理亲近感。诗歌意境之于沧海兄画及,正有提升、丰富、深化之效。具看沧海兄自己的说法:
逆承者主要着眼于艺术精神的现代性,对传统中与时代精神“不符”的因素,趋向于彻底地丢弃,但这里做法的危险在于:离开传统,往往割断了文化精神的血脉。在创作过程中,少了些修养的厚度,少了些情境,更缺乏应有的生动。
沧海兄似自觉继承了乃师范曾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在中国当代画家如何自觉、完善地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以之丰富和提升其艺术作品之文化内涵与精神境界这一点上,沧海兄的艺术实践应当对同行具有较普遍的启示意义。
三
在当代中国写意画领域,沧海兄又以自觉、突出地融会禅意、禅趣、禅境而个性卓然。若更具体地言说沧海兄写意画主题,则不得不提及他的禅宗写意画。将佛家禅宗意趣引入写意画,将禅家智慧与画家写意理念相融合,此正沧海兄区别于其他写意画家之处。不能将沧海兄的所有画作尽归于禅宗写意;但是,禅宗写意确实是其画作中一个很突出的主题,也是他很用心的一个领域。他在此领域的探索是很自觉的:
禅宗的“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如老庄“自法自然”、“复归于婴儿”一样,都是旨在讲述人的自然本性回归的途径,而写意花鸟画自身的自然性的特点,首先要求写意画家回归到自心,回归到万物齐一的境界……写意花鸟画发展的复归自然之道离不开对传统精神的再认识和学习,而禅宗写意画的精神,不仅仅对古代,更对现代写意花鸟画的创作有所启迪。
作为一个画家,沧海兄对佛教文化因素之引入,有几种形式。首先是他的佛教题材人物画,诸如《伏虎罗汉》、《调猿图》和《降龙罗汉》。需注意者,即使是佛教人物画,沦海兄也在其画面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了一种文化交融,比如《虎啸千山》和《镜中影,水中月》中佛教人物与大山水背景之融合,可谓是一种庄化释家的处理。其次,以物象、物境之感性手段阐释佛家法理,当是其禅宗写意画之重镇。在此方面,《诸法空相》也许可算是一个典型。画家在此以淡墨薄影呈佛家之空观,使惯常的水墨绘趣味在“诸法空相”题名的暗示下陡然幻为形而上境界,引人由现象界之常境顿转为对现象界之空观,使观者于刹那间洞观色界依它起性之佛家真谛,进而放世俗之执着、依恋心,起佛家之禅观、智悟心,此正佛家借画艺色相方便说法之本旨,故可谓成功佛教艺术之典范,它如《说因缘》、《诸无无法》均可作如是观。
值得注意者,即使是平常物象、物境,一经沧海兄禅偈式品题,画面之格调与内涵便判会然顿改,别开洞天,由凡入禅,岂不怪哉?此可举《性静元如日月明》、《莫谓无论心便是道》和《阿耨多罗》、《石榴》为例。其变换之巨、效果之妙,几近于杜尚对小便器之品题,堪称文字、哲学、宗教影响艺术品内涵之范例。一幅《前身合是此山僧》,似足可表达沧海兄对禅境佛法之深刻情感。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此作视为画家之自画像,它正好呈现了沧海兄内心深处的佛结。沧海兄曾数次入深林古寺与佛家之大德高僧共同参禅,同画共题,此类故事足可为深入理解海兄禅宗写意画之资。
何谓禅趣禅境?浅表言之,似可归结为对佛旨佛法之独特爱好。沧海兄画作中也确有明确地宣示佛家教言者,前例已示。深入言之,禅家趣味实乃一种精致的思维之途与上乘的精神生活品类。简言之,它是一种直觉智慧——面对日常生活世界之万千感性殊相,当下参悟其内在关系与普遍本质的哲学顿悟。在此意义上,禅宗写意画所表现出的禅趣味,并非旨在彰显佛家教理之特殊宗教趣味,实乃一种具普遍精神价值之思维操练与形而上哲思追求。于是,于绘画中引入禅宗理念,实际上是艺术家在感性精神世界中引入超感性的哲学意趣,因此,写意画与禅宗思想之融合便是为艺术的感性、殊相世界引入哲学、智慧的因素,它可使绘画意境增加哲学高度与形而上品格。某种意义上,它是对写意画的一种丰富、拓展与提升。
在道家思想影响下,禅家视野往往与道家视野高度重合,更喜欢在物境,而非人相中呈现宇宙本相、佛家智慧。沧海兄的禅宗写意画,每喜用“以物观物”的非“我执”视野,为天下万象写真,于画面中呈现寂静、旷达之物象、境界,引导观者在静观物象中超越自我,融入万象,或得物无自性之佛家空观,或得物我齐一之道家意趣。无论何者,均可谓超我之境。沧海兄每喜以物象、物境揭禅趣,此可以《莫道山中岁月长》、《春江花月夜》、《幽人应未眠》、《不知有汉》等为例。
径以禅趣论沧海兄的画境也许是偏至之论,因为我们从其画作中,又每能发现庄子身影、庄子情调。其《独应于无人之野》、《啸歌乐往年》和《林逋诗意》等幅所呈现的,便是典型的道家纵情山水,适应逍遥境界。李泽厚先生曾庄禅并论,可谓慧眼独具。确实,自魏晋起,士人之欲追求自由、超迈境界者,无不优游于道释间,其间之异已为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其间之同正为其所神往。
这是一个中华民族再次实现文化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华民族更为成熟、自信地面对世界、认识自我的时代。当代中国人正同时面对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双重主题,沧海兄作为当代画家群体中之一员,真诚、执着地继承传统,阐释传统,发扬传统,以其全部的勤劳、智慧与才情不断为社会贡献出同时具有民族文化血脉和艺术家自身个性的作品,持续地在写意画这个领地耕耘,为我们创作出既有传统文化基因,又具时代烙印、新鲜活泼审美感染力的画作。这是画家本人,乃至我们这个民族自信、成熟的标志。画家前景广阔,中华传统艺术、传统文化前景无限。我真诚地为沧海兄祝福,为中华民族祝福!
2012-9-29
作者简介:
薛富兴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美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美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天津市美学会第六、七届理事会会长,中华美学会理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6),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哲学系访问学者(2007-2008)。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中国美学和环境美学研究,学术兴趣兼及中国哲学与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