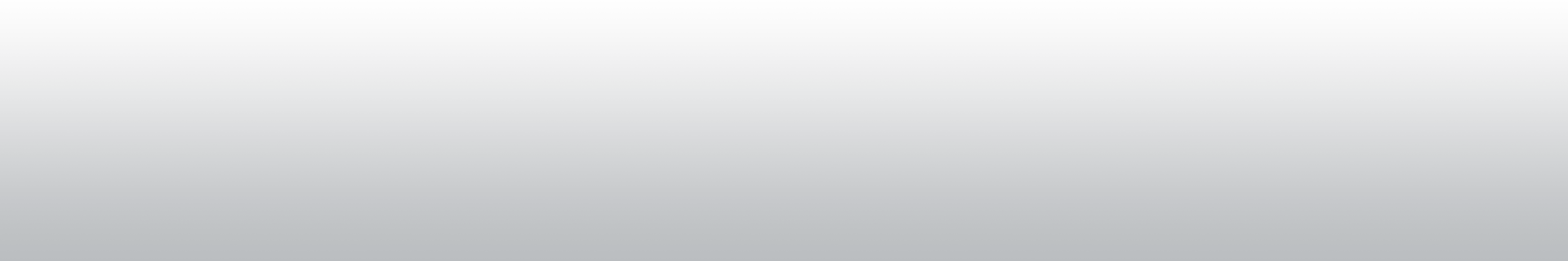一曲理想主义者的无尽挽歌
——读司马迁的《伯夷传》
薛富兴
司马迁的《伯夷列传》是历代隐逸传之祖,伯夷与叔齐因此也就成为古代隐士的伟大先驱。提到隐士,我们自然会想起庄子,庄子为隐逸生活方式提出了雄辩论证,因此我们也就倾向于将整个古代隐逸传统视为是对庄子道家思想的忠实发扬。比如,根据庄子的逻辑,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为何会拒绝当国王呢?那是因为他们嫌当官儿太累人,不自在,所以他们宁可将这种万众瞩目的尊荣让给别人,自己却兴高采烈地流浪远方,去做一番“逍遥游”。《庄子》里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比如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逃跑;商汤让天下给务光,务光发怒。在儒家传统中,被视为最高政治美德与最理想政权交接制度的禅让,被庄子改造为对政治权势与社会责任的清高唾弃。但是,就《伯夷传》文本而言,庄子式的解说似乎并不合套,伯夷、叔齐并不是庄子思想之先驱,反倒是儒家政治、道德理想的典型。
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为孤竹君之子。父亲本来选定叔齐为接班人,等父亲去世后,叔齐却以伯夷是兄长为由,执意要将继承权让给兄长。伯夷则拒绝了弟弟的这番好意,拒绝的理由是“父命难违。”结果,叔齐也不肯继任,最后他将继承权转让给老二,与大哥相约离开故土,自我放逐,过起了流浪生活。
从《伯夷传》极有限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王位继承制度中一对深刻矛盾,这就是“立长”与“立贤”的冲突。王制继承到底应当遵循怎样的游戏规则?“立贤”与“立长”都很重要,但很难结合在一起。若从操作的简易性角度讲,以年齿论资格,即“继位以长”这条形式化标准最省事,最难起异议,可谓硬标准;但若从王业之未来质量看,以德性与才能论继承权,即“继位以贤”则更为内在,更为合理。可是“贤”的内涵太丰富,随意性太大,最易引起异议,会引起太多人的心理幻想,弄不好会引出新的政治风波。
显然,叔齐与乃父在王位继承规则上有分歧,其父没有将王位传给老大,而是传给了他这个老三,显然并未遵传位以长之例,或者说,传位以长尚未形成定制。可是,传位以长在当时肯定也很有权威性,否则叔齐也不会用它作让位理由。
伯夷与叔齐代表了两种王位继承观念——“立长”与“立贤”。初看起来,在这种重要政治观念上,弟兄二人截然对立。可奇怪的是,最后他们又做出相同的选择。为了让新继承人彻底放心,他们干脆离开故士,自我放逐,去作隐士。在选择当隐士这一点上,他们又高度一致,是真正的志同道合者。
伯夷、叔齐本来并无尚隐之趣。若有,他们完全可以在继承问题出现之前就去逍遥游,像庄子所倡导的那样。他们是突然面临继承王位这一迫切任务时,才不得已做出如此选择。突然出逃是因为他们面临着巨大的两难选择。先说叔齐。父亲的安排显然出乎他的意料,否则他完全可以兴高采烈地上任了。他是老三,而父亲却选择了他。他毅然将王位让给兄长,说明父亲的选择违背了他的政治理念。是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德性与兄长相差太大吗?父亲弃长而立幼说明叔齐属于贤者。关键在于,依叔齐,“立长”才是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理想的政治制度——“立长”,他毅然拒绝了父亲传给他的王位。再看伯夷。叔齐的让位也当出乎他的意料。他坚决地拒绝叔齐的让位请求,表面上是因为“父命难违”,实际上则是因为他与父亲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立贤”。
伯夷与叔齐二人看似相反,实则相同。一方面他俩在具体的政治理念上存在差异——一个赞成“立长”,一个赞成“立贤”。
伯夷、叔齐可以说是殉自己心目中的政治理念而死的悲剧人物。在那个时代,各诸侯国的王位继承,既有“立长”者,也有“立贤”者,尚未形成定制。因此,这两种制度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二者间分不出善恶与优劣。这倒是很符合黑格尔的悲剧观——都有自己合理性的对立双方走到一起,虽然造成冲突,但很难分是非。悲剧之揪心、无奈、深刻处,正在于斯。
但是,在更高的政治、道德理想层面,他们相同的,这就是他们都能为了坚持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信念,主动放弃就在眼前的物质利益,是典型的为义而弃利行为,两个人都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差别,他们无需让位;没有共同点,他们俩也不可能结伴而出隐。
伯夷、叔齐兄弟的理想主义在商周革命的社会浪潮中再次得到表现,其儒家式的温和变革理想放射出人道主义的灿烂光华,最终以自我毁灭的悲剧形式成全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他们有幸而生活在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这使他们的政治理想有机会被放在时代的天平上称出份量;他们不幸而生活在一个人类依然崇尚暴力对决的时代,他们的生命,连同他们所看重的文明理念,被历史的洪流无情地冲刷而去。
伯夷、叔齐离开故士后,因慕文王姬昌善养老之名而来到周的地盘。不巧的是,他们刚入境,姬昌就过世了。武王姬发捧着文王木主发动了征讨商纣王的战争。伯夷、叔齐二人闻讯,就来到大军前,拦马劝诫周人。他们说商纣王的暴政已然让百姓受苦,你们不该再发动战争,让老百姓罪上加罪。纣王诚然无道,可你们用粗暴的手段,即使真的从暴人手中夺了政权,也没有合法性。纣王现在还是你们的王,你们还是他的臣子。作为一个臣子,不该犯上作乱,反对当今圣上,为后人开恶例,等等,等等。当时武王一方力强气盛,势在必得,听了这番不得革命的话,当然很不高兴。武王手下的人很气愤,要将二人抓起来给杀了,幸亏太公姜尚在旁,为他们说情,才给放了。
显然,伯夷、叔齐是一个绝对的政治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本朝之内的王位继承,还是不同政权之间的交替,都应当理性、温和地进行,应当人道、文明地进行。拿商纣王来说,既然自己已然失去了德性与民心,他就应当主动把权力让给新的有德者。拿周武王来说,即使商纣王拒不相让,那你也不能从人家手里硬抢啊,抢来的东西还有什么合理性,这使本来合理的东西也变成了不合理的了。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既然我们兄弟俩可以将王位让来让去,为什么你们就不能也相互地谦让一下,表现一下高姿态呢?这可真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请千万别嘲笑这兄弟俩的天真。难道他们所主张的不正是我们应当切实施行的吗?难道他们俩自己不是已然实践在前了吗?我们没有资格嘲笑他们,我们既不能从道德上否认其政治理想的崇高性质,也不能证明自己做得比他们更好。面对这样的正人君子,我们应当感到的是惭愧,而不是高明。如果我们嘲笑了他们的理想,我们就是在扬恶惩善;如果我们内心无半点理想的光辉,我们就会活得心如死灰。如果我们不愿为理想有任何付出,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暗夜。
让兄弟二人大跌眼镜的是,武王姬发居然取胜。纣王暴虐多年,民实不堪,所以姬发振臂一呼,天下归心。不管愿意承认与否,他们现在已经是周人了。怎么办呢?普天之下,莫非周士,他们又飞不到天上去。想一想自己心目中“不犯上作乱”、“不以暴易暴”的神圣理念,他们还是心有所不甘。无奈之下,他们决定逃到今天山西永济的首阳山里,拒不领周王朝官方发给他们的口粮,自己采野草充饥。人类毕竟不能完全返回到原来的食草动物状态。所以,这对义人最后还是饿死在首阳山。
临死时,他们曾作歌一一首,其辞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命之衰矣!
这是一曲理想主义的哀歌。主人公认定自己所坚持的政治理念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但他们又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坚持理想并不属于这个时代,而只是一个已然逝去了的遥远旧梦,自己已然与周人决绝,理想已不可能实现,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理想都没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伯夷、叔齐并非无所作为、消极避世的隐士,他们是敢于信守、敢于付出,有大义大勇的侠客。他们是真正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伟岸君子,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宣扬着自己的政治文明理念。他们为人类的政治、道德树了一个很高的标杆,我们可以承认自己没有做到,但无论如何不能否定其理想的崇高性质。人类文明史上也幸亏有了这样的标杆,它可以随时照出我们自己的发展水平,照出我们应当前行的方向。
造成当年伯夷、叔齐人生困境,使他们不得已而出逃的政治制度——“立长”与“立贤”的矛盾,已然成为历史陈迹,他们所坚持的绝对地不可以“犯上作乱”的信条,也不再能束缚今人。但至少有一点,他们所苦苦信守的“毋以暴易暴”,在今天并未过时。一国之内的政治如何交替,国与国之间利益冲突如何解决?这仍然是我们今天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我们已然熟悉了的是斗争哲学,对方的不义似乎是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充足理由,只要对方不义在前,自己的不义似乎也就成为义举。我们总以为目的善可以为手段恶辩护。其实,狄更斯在《双城记》、雨果在《九三年》对法国大革命时代暴政的反思正说明:目的善不仅不能代替手段恶,相反,手段恶往往会转化为实质之恶。“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并非不合时宜的老调子,用今天的话说,它关乎政治文明,是一个人类是否有能力用文明、人道的手段解决重大利益冲突的问题。功利主义地为一时的“以暴易暴”行为辩护,自以为得手,最终都会得到效仿者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应,东西方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在《伯夷传》的结尾处,司马迁从哲学的高度反思了伯夷、叔齐的命运。他是由这对兄弟的悲剧对历史老人提出质疑。常言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像伯夷、叔齐这两位应当算是善人了吧?他们志行如此高洁,最终却被饿死。再联系到孔子最欣赏颜回,颜回却青年夭折;大盗柳下跖暴行无数,最后却得了个善终,这到底算怎回事呢?
司马迁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以孔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及“举世混浊,清士乃见”来做答。那意思是:善恶都是一种个人的选择。选善从善,选恶从恶,每个人都以自己愿意的方式生活好了,不必强求最后结果之善恶。若无世俗之恶,怎显君子之善呢?
如果立足于伯夷、叔齐二人的心理状态,司马迁的这种解释是准确的,出逃与隐居,都是二人的自愿选择,这对他们的最初意愿来说可谓求善而得善。但是,司马迁并没有回答自己所提出的正面问题——历史老人到底有无善恶,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善恶?
司马迁的回答正在不言之中。根据他举出的例子,我们似乎只能得出善恶颠倒,至少是无所谓善恶的结论,可司马迁又没有明确地将它说出来,而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将话题转移到“道不同不相为谋”上,这意味着司马迁似乎不忍公开地主张道德虚无主义。这正看出他内心的矛盾,见出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公开地主张善恶颠倒,善恶之分多余,历史后果必然是丛林原则盛行,人类历史会堕入大恶的深渊。如此游戏规划与人生信念只能使极少数强人受益,大部分弱者受损。因此,善恶之分与扬善惩恶,虽然不能严格控制恶行,它至少是善恶冲突的减压器。没有了这个减压器,我们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善恶的平局,而是恶对善一边倒式的决定性胜利。此为任何一个有社会公德心、责任心的历史学家所不忍。其实,儒道之分野正在其斯。儒看似愚腐,实则仁厚;道看似潇洒,实则阴冷。以此读庄生之《逍遥游》,可谓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