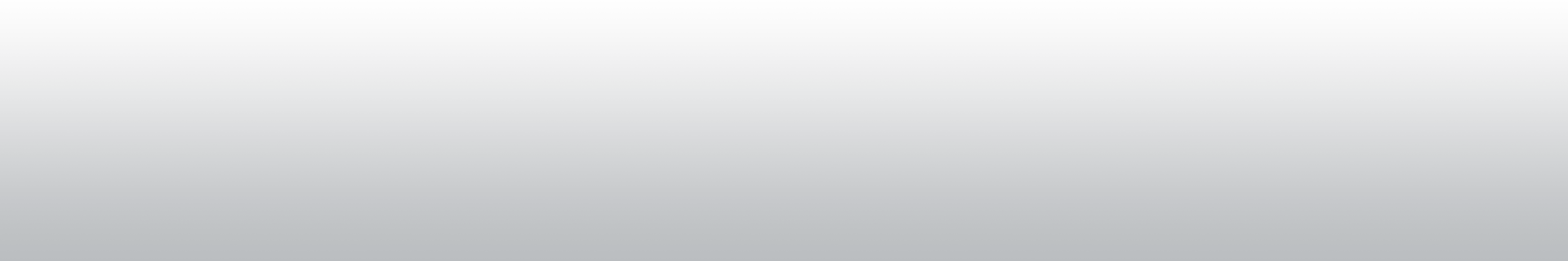一代英豪 千古绝唱
——读太史公《刺客列传》
薛富兴
刺客是历史人物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太史公在《史记》中特别地为他们立传,为他们勾勒出一幅简约的肖像画,引后人深思。
一
曹沫是刺客群体中第一位出场者。与后面几位同仁相比,故事虽然简单,却也漂亮,为刺客群体成功亮相。
曹沫是鲁国人,因有过人气力与胆略为鲁庄公效力。庄公很欣赏他,任命他为将。曹沫率鲁兵与齐国战,三战三败。庄公只好割地求和,但仍然以之为将。后来,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正当两国首领端坐坛上时,曹沫突然手持匕首,将桓公劫为人质,逼桓公归还所掠之地。情急之下,桓公只好当场答应。事后桓公欲反悔,然而管仲则以为:在国际舞台上答应了的事,最好不要食言,否则有违大国形象:“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不如与之。”齐国最后只好尽归所略鲁地。
作为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曹沫也许不是合格人选;但他确有过人之处:这便是他的气力与胆量。无过人之勇,断不敢在诸侯会盟时节外生枝,劫持大国首领;无过人之力,此事恐怕也难以得手。曹沫绝非仅靠勇、力取胜。从事后的结果推断:他之所以敢出此妙招,大概他事先已研究过大国心态,研究过桓公身边的重要人物——管仲。因此又可谓善于谋略之人。刺客群体中,后面几位勇士均以失败告终,曹沫乃惟一成功了的刺客。也许还要加上更重要的一项——运气。其后继者在职业技能——勇气与搏杀能力上也许并不逊于,而且还可能优于曹沫,但他们之所以未能成功,也许就差了一点曹沫所碰到的运气。所以,在刺客群体中,曹沫真的是个幸运儿。
比之于其成功经验,探究一下曹沫当刺客的心理动机也许对我们更有意义。在曹沫的故事中,司马迁虽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曹沫以为,庄公对他有知遇之恩,因此他要知恩图报。曹沫以勇武著名,恰好遇上庄公亦“好力”,因而任他为将。曹沫作了将帅,带兵打仗,却战三战三败,自以为大愧主恩。即便如此,庄公没有嫌弃他,而是继续以之为将。三战三败的职业耻辱感与庄公对他始终如一的信任,从正反两个方面在曹沫的心里聚会,最终促成曹沫以非常之手段报答庄公的决心。结果,他在战场上失去的,又从外交场合出奇制胜地抢回来,既找回了面子,也报答了庄公。
士为知己者死,知恩图报。曹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已经宣示了春秋战国时代刺客群体的道德主题,它以夺目的光彩,映彻历史时空。
第二位出场的刺客是专诸。他本来是伍子胥报复吴王僚的一个工具。伍子胥初说吴王僚以伐楚。吴王不纳,后知公子光有异志,欲取父而代之,故将专诸荐之于公子光。公子光得专诸,九年而“善客待之”,终得专诸之心。后公子光设宴招待父王僚,席间,专诸趁奉肴之际,用藏于鱼腹中之匕首,替公子光杀死了父王,专诸自己也死于乱战之中。后公子光立,是为阖闾,封专诸之子为上卿。专诸之效死力,似乎就为了报答公子光九年的款待。非也,最终促成专诸行动的,是公子光的一句话:“光之身,子之身也。”这便是刺客们的心理软肋——“只要一句话受用,俺这命也舍得给你!”
二
刺客群体中,最让人感伤心、震动的,当数豫让。
豫让,晋人也。曾事范氏与中行两家,未得二氏赏识,转求于智伯,智伯恩遇之。后智伯为赵襄子所灭,豫让逃于山中,决计为智伯报仇。他隐姓埋名,接受了宫刑,混入赵襄子宫中。一次,豫让怀藏匕首去粉刷厕所。赵襄子如厕,不由心中惊悸。下令捉拿刷厕之人,发现正是豫让。豫让手持匕首坦言:“我就是想为智伯报仇。”左右欲杀豫让,赵襄子曰发话:“这是个义人啊,我自己小心点就是了。智伯已没了后代,可他的臣子却不忘为他报仇,这真是个义人啊!”于是放了豫让。
此后,豫让用漆毁了容,吞炭弄哑了嗓子,使人们无法辨认。在街上行乞,连他妻子都没认出来。一次,得知赵襄子要出行,豫让潜伏在其必经之桥下。赵襄子过桥时,马受惊跃起。赵氏曰:“一定是豫让藏在这里。”使人搜桥,果得豫让。赵氏生气地质问:“你不是曾为范、中行两家卖命吗?智伯灭了二氏,你却转而又为智伯效劳。智伯现在已死了,可你为什么还老是要为他报仇?”豫让说:“我为范与中行二氏服务时,他们拿我当一般人对待,我也就用一般人的方式回报他们;但智伯却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用国士的方式报答他。”赵襄子感动得为之落泪:“豫让啊,你为智伯所做的一切,已成就了你的美名。我前次放了你,也对得起你了。这次你还要杀我,不能饶你了!”于是,众兵围了豫让。豫让说:“我知道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为美名而死之义务。上次你已放了我,天下都因此而称你为贤。今天的事,我当然自认死罪。可我还是想请你把你的衣服拿来,让我刺一下,以满足我报仇的愿望,我死而无憾,其它的也就不敢多想了。”赵襄子激赏之,让人把自己的衣服拿给了豫让。豫让拨剑三跃,刺穿赵衣,大呵一声:“我算是报答了智伯!”然后伏剑自尽。
豫让两次为其主报仇,终因差了点儿运气而未果。但他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则极其沉重。先是自残,然后是毁容,抛弃了家庭则更不待言。豫让的故事,让我们感动的并不是其命运之蹇——运气总是差了点儿,不像前面的曹沫一样;而是豫让绝意报仇的那种坚决意志。诸多磨难都是豫让的自觉选择,是其自由意志的结果。豫让与曹沫不同。如果说曹沫之劫持齐桓公,还有其个人的原因——与齐国三战而败,丢了军人面子;那么豫让与赵襄子之间,根本并无过节。豫让要报的并非自己的仇,而是智伯的仇,是替别人报仇。表面上看来是报仇,但是,复仇并非豫让行动的最大心理动机,因为赵襄子与他本人无仇。豫让行动的最大动力是报恩,是要回报智伯对他的知遇之恩:“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用国士的方式报答他。”他是用复仇的方式来报恩。
知恩图报,这便是当时刺客群体的最高道德理念。正是这一崇高的道德理念,支持着豫让,使他能不计成本地践行着自己的道德理念。西方伦理学传统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功利主义,注重道德行为的因果联系,特别是关注结果。其实,豫让在寻仇过程中已经意识到成本问题。第一次报仇失败后,他被一个朋友认出来,朋友曾为他找到一条成本较低的方案:“以你的才能,如果委屈一下自己,转而为赵襄子效劳,赵襄子一定会待你不薄。如果你因此而得到了亲近赵襄子的机会,那你想干什么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因想杀赵氏而将自己毁容废身,这不是更增加了复仇难度了吗?”你猜豫让怎样回答:“既然已经决定做赵氏之臣,而又算计谋杀他,这是用二心来事君。我也知道自己的计划很难现实,但我之所以还是决计要这样干,就是要让天下以及将来的以二心事君者惭愧!”看来在豫让的心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忠”是第一位的,不能为了降低报仇成本就违背了忠的原则。正是忠——忠人之事、忠心不二,与义——受恩图报这两个道德观念支撑着豫让的复仇事业。他宁肯增加难度与风险,也不做违背原则的事。在这一点上,豫让的精神状态更接近康德的道义伦理学——道德命令是绝对的,不能因功利效果而与道德原则讨价还价。一旦意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一旦在心里接受了道德原则,就要严格地去执行它,不管它是否能给我们带来幸福。
更让豫让为难的是,虽然他的报恩行为是正当的,而他面对的复仇对象——赵襄子也是一位义人。比如说,人家第一次就放了他。那么,第二次的报仇还该不该去呢?他去了,看来,还是报仇的意志占了上风。但是,面对命运的安排——赵襄子还是发现了他,他只好认命了——“非所敢望也”。
当他意识到寻仇以报恩的正义事业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时,豫让又做出了惊人之举——你能不能让我刺一下你的衣服,让我象征性地了结心愿呢?让今人吃惊的是,赵襄子真的满足了他的愿望。当豫让万般无奈下,围绕着赵襄子的衣服,三跃而起,击之刺之,大喊一声:“智伯啊,我这样也算是给你报了仇,”然后伏剑倒地时,我们每个人都被震撼了。这便是典型的命运悲剧。豫让为了一个心中的崇高道德理念——忠义,真的尽力了,但还是没有成功。他虽败而犹荣,因为后人无法否定他所信奉的道德理念,失败的只是他具体的事业——复仇,胜利的则是他所信奉的道德理念。许多人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悲剧。有的,豫让的故事即是典型。它既符合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英雄竭尽全力,但最终命运弄人,未能成功;也符合黑格尔关于悲剧的理念——两个都有正当性的理念发生了冲突——豫让的报恩是正当的,但豫让要杀的赵襄子也是义人。豫让最后的象征性复仇意义非凡。太史公大概想表达这样的意思:豫让报仇的具体事件可以失败,但是,豫让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忠义则要得到世人的尊重。
对于刺客群体的心理动机,豫让表达得最为晓畅:一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待我不薄,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就是死也心安了!”又曰“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我也要用国士的方式报答他。”这说明刺客群体一方面自我意识极强,他们充分地知道自己的价值,同时也要求社会正确地认知他们的价值。凡是能正确地认可其价值,并以物质的和精神的方式体现出对其价值的充分尊重者,必然会获得刺客们全心全意的服务。这里传达出两种信息:其一,个体的生命价值,每个人自我实现的欲望。应当说,每个人都具有被身边人认可的心理需求,而刺客群体作为心身能力俱佳的精神群体,在这方面更为自觉,要求更高。春秋晚期,周天子失御,诸侯雄起,客观上刺激了“士”群体之崛起与自觉,苏秦、张仪所代表的是文士,即凭突出的知识与智慧获取功名的群体,豫让及后来的荆柯所代表的则是以过人武艺、勇气、胆识服务于诸侯们的群体,即武士群体。在当时的文士群体中,更普遍的是张仪之类,身挂六国相印,有奶便是娘的群体,他们的智慧是卓越的,但在道德上则乏善可陈。刺客群体则不同。他们的精神魅力并不在其超凡神奇的武功,虽然这确实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如果他们真的只有武功而没有道德原则,像李逵一样只知道一时兴起,挥斧乱砍一气,那么则他们只是一群魔鬼而已,让人恨还来不及,太史公怎么会专为他们立传?刺客这个特殊的武士群体之所以能在历史上放射出永恒的光芒,乃是因为支撑其武功背后的崇高道德理念,是他们所信奉的道德理念的价值,以及他们为此崇高理念坚持不懈、不计成本,生死以之的信守、践行之德感动了后人。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能把这群刺客只当一群武士对待,而应当同时将他们也视为文人,因为他们也具备了文人所看中的人文价值与德性;而且,在对正面人文价值理念的坚守与践行方面,他们比当时绝大多数文士做得还好。知识与智慧诚然令人激赏;但是,若拿它们与崇高德性相比,不免逊色许多。读刺客列传,我们才真正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崇高地带,才真正领略到后人为何有“尊春秋道德”之论。在当时,真正认真地践行夫子伦理教言的,也许并非苏秦、张仪之类文士,而是豫让、荆轲这样的武夫,面对这个伟岸群体,其忠诚,其纯粹,其血性,其胆略,当然还有其不凡的身手,真真地让人敬服、热爱、怜惜。在他们面前,多少士子当含羞,因为对于圣人的教言,他们应当远比刺客们知道得多,也懂得多啊!
太史公也是一芥书生,从他叙述这个群体行状的文字中,我显然读出了老人家对刺客们发自内心的崇敬与激赏。真心地感谢太史公!正是凭了他的如椽巨笔,我们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这样一批有胆有识、有德性、有抱负,有血性、敢践行,为实现理想不计成本、有恩必报的仁义、豪杰之士,与这些畅快淋淋地挥洒自己的人生,真正地潇洒走一回的汉子们相比,精心地算计第一天行为的每一分得失的商人,以及甘心以大半辈子夹着尾巴做人的代价,换取所谓最后成功的智者,真是卑陋之极。刺客们的传奇最为浓郁、深厚,最令人荡气回肠。他们的行状,映射出人心的忠诚与信义,达到了人类道德理性所能达到的至高点,故而他们的生命之光如灿烂星河,划过夜空,令后人永久景仰。
三
第四位出场的是聂政。政本轵(今河南济源)人,有杀人前科,为避仇来到齐国当屠户。韩哀侯时,韩国的严遂与国相侠累傀不和,严氏恐得报复,故逃离韩国,到处寻访能为他除去侠累氏的合适人选。到了齐国,有人向他推荐聂政。其时,政虽离井离乡,混迹下层,可仍很有名:时人誉之“勇敢士也”。严氏数次备礼拜访聂政。一次,他带了重金、旨酒来到聂家,说是要为聂母祝寿。聂政惊其礼厚,严氏则坚请笑纳。聂政说:“我现在虽然家贫,寄居他乡,但尚有老母在,所以不能为您效劳,请回吧。”严氏曰:“我有仇家,遍游诸侯寻访壮士,想请人为我报仇。只是到齐国才得闻您的高名。带来这些礼物也只是想与您交个朋友”,最终将礼物留下。
数年后,聂母逝。聂政安葬了母亲,除了孝服,便主动来找严氏:“以前我所以不能答应您,是因为我尚有亲人需要供养。现在亲人已逝,没什么负担了,可以为您效劳了。请说吧,您的仇家是谁,我替您办了他!”仲子交待:“仇家乃当今相国侠累氏,他又是当今韩王叔父,人多势威,身边总有众兵把守,别人很难靠近他。您若答应替我做这件事,我要给您多备车马壮士,助你一臂之力。”聂政深不以为然:“正因如此,才不宜人多。人多嘴杂,易生枝节。”于是,聂政告别了严氏,独身前往。
未久,聂政来到韩国,得着机会。其时,侠累正端坐府上。虽然堂上有众多军士守卫,可聂政仍得以挺身闯入相府,成功击杀侠累并身边数十人。怕事后被人认出,累及他人,聂政于堂上决目剖腹而死。
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街头,并悬重金征集知情者,未果。
聂政的姐姐聂荣闻其事,推想此事定乃聂政所为,于是来到韩国,伏弟尸而当街哭喊:“吾弟聂政杀了韩相!”街市上众人大惑不解:“韩王正悬重赏捉拿凶手,你怎么不打自招,主动告发自己的亲人呢?”
聂荣答曰:“以前吾弟屈居市井间,是为了扶养母亲和我。母亲去世,我出嫁后,严遂不因吾弟存身卑微而与之交,发现了他,赏识他,待他不薄。吾弟此举当然是为知己者献身。他为了保护我,才主动毁身弃名。现在,我怎么能为了避杀身之祸而埋没吾弟之令名呢?”于是,号天长叹,哀绝于弟尸旁。
所有刺客都有共同的心理动力,那就是为知己者死,知恩图报。且听聂政的内心独白:“政本来只是一个操刀宰肉的市井之人。严遂则贵为一国之卿相。他不远千里,屈尊与我相交。我在此前也并无大功,对严氏之回应也只算一般;但人家却以重金为我的母亲贺寿。我虽然不接受人家的礼,但从其行为中可以见出,他对我的价值是有深刻了解的。严氏这样的贤者因心有不平之意而宁肯到下层信任我这样的人,我能没有任何回应吗?”可见,聂政对自己的才能,虽有高能大德却不得不屈居市井的处境,以及严遂这种贵族人士对他的赏识,都很在意。
聂政的故事又有新意趣。首先,决定替人报仇前,聂政特别看重尽孝的人子义务,直到母亲逝世后,才答应为严氏报仇。在这一点上,聂政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因为他严格地践履了《礼记》上即有“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之规训。作为一个刺客,他努力做到尽孝与报恩的平衡。其次,为保护亲人与朋友,聂政完成任务后,主动毁身自杀。一般而言,刺客群体不仅重视德性,同时也看重荣誉。某种意义上,荣誉还是他们做出英雄行为的重要动力之一。聂政自动毁身,就等于他不仅为朋友献出生命,同时也放弃了出名的机会,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次壮举的主角。
聂政的故事因其姐姐的发扬更令人浩叹。在这里,黑格尔的悲剧观念再次得到印证。这是两种正义观念的内在冲突:聂政为保护亲人和朋友而自毁;但其姐聂荣为不委屈弟弟的令名而主动告发了弟弟。这种告发表面上看是不义的,有违社会一般习俗与道德要求;但它却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弘扬弟弟所尊崇的道德理念。聂荣的选择与其弟表面上看相反,但实际上却在更高的层次达到了一致。这种告发并不会给其弟带来灾难,因为他已死。可是,为了成全弟弟的令名,聂荣却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因此,聂政故事的主角,实际上是双雄——聂氏姐弟。姐姐聂荣虽然没有参与刺杀行为,没有刺客所具有的职业技能;但是,她却具有刺客体群体所拥有的精神内涵——重德轻生。她完全具有侠客所具有的胆略与德性。因此,我们乐称其为姐弟双雄。聂政的故事若无聂荣的续写,会有更大遗憾。作为一个刺客,聂政功成而身死;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现在,聂政之英名因其姐聂荣而终于得以传扬。然而,即使最后意未能传扬,有了一个如此侠肝义胆的知音姐姐,聂政亦死而无憾,可含笑九泉矣!
四
荆轲在刺客群体中最后一个出场,情节也最为波折。
作为一个英雄,荆轲是幸运的,他有幸出生在一个天下多事,豪杰们必将有事可干的年代。其时正当战国晚期,那是一个秦国即将扫灭六国,诸侯们亟需各路好汉,以便做最后一搏的时代。
轲本卫人。他与前面诸位刺客最大的不同,似乎在于他是一个文武兼备的高人:“好读书、击剑。”他曾“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此“术”当为文术、国术,即“合纵”、“连横”之类的权谋、诈术,今所谓“国际政治”者也。荆轲本乃苏秦、张仪同类,因其文术不售,不得已才走上武侠道路。时事成全英雄,英雄涂抹时代。值此天下多故,时局动荡之际,荆轲十分自信地仗剑走天涯,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他注定不会寂寞。
作为一个书生,荆轲来到燕国是要干大事儿的。他虽然嗜酒,而且当地人好像总可以看见他在市井间喝得烂醉,围绕在其身边的,似乎都是些宰狗卖肉之人,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太史公评曰:“其为人沈深好书”。就是说,荆轲骨子里是一个深沉内敛之人,而且识多善思,长于谋略。实际上,荆轲有另一个交际圈:“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他周游列国时,到处结交朋友,故而社会资源积累丰厚。来到燕国后,他虽然也结识了以宰狗为生,却有点儿不俗,爱好音乐(“善击筑”)的高渐离这样的朋友;但其社交重点则是此三类人物——“贤、豪、长”,即有德者、有势者和有经验阅历者,这些都是做大事必备的人力资源。他的传奇便从他认识了一个同类——处士田光开始。田光很有眼光:“知其非庸人也。”
未久,燕国面临即将被秦国吞并之危境,太子丹无所措手足,问计于乃师鞠武,鞠武推荐处士田光。太子召见田光,光言己已老,不堪大任,又荐荆轲。
荆轲之出场,不可谓不隆,先有太子师鞠武,后有处士田光为之铺垫,颇似后来诸侯孔明出场前之先有徐庶与庞统。太子丹能不对他寄以厚望吗?荆轲终识燕太子丹,一出壮烈悲凉的戏剧得以开幕。
作为一个政治家,燕子丹对当时天下大势的整体判断是正确的:强秦兼并六国已成不可阻挡之大势:一方面秦国欲望无限,必至尽兼六国而后止;另一方面,六国已被强秦吓倒,未敢合纵以联合抗秦。因此,对燕这样的小国而言,为秦所灭只是时日而已。而且,上天留给燕国的喘息之机也不多了。因此,目前自救的惟一希望便寄托在创造机会,主动地节外生枝上——效法春秋时曹沫故事,派壮士以利诱秦,劫持秦王。上策是劫持成功,逼秦退兵。若生擒不成,亦可刺杀之,给秦国造成一时无主之混乱局面,六国则可乘势联合,再谋抗秦。在今人看来,此计实不足以阻挡秦并六国之势,因为即使刺秦成功,秦国仍可推举新主,完成统一天下大业。但从战术层面讲,若命运女神真的眷顾六国,刺秦成功似可滞迟秦国并六国速度,甚至亦可逼秦国暂时吐出一些进口之食。
世有燕太子丹而后有荆轲。荆轲刺秦故事中,毕竟太子丹才是主谋。如果太子丹如乃父——燕王喜一样乐于坐以待毙,或像其它诸侯王一样提前认输,他也就不会有此奇谋,荆轲也就根本没有出场的必要了。诚然,绝大多数政治家是实用主义者,面临胜败定局,不会再做无用功。但是,若所有政治家均如此,人类历史便如已有了标准答案的应试一样索然无味。幸亏并非如此,历史上总有一些具备好听些说是诗人,不好听些说是赌徒气质的政治家,面临天下大势,仍然愿知其不可而为之,愿再赌一把。如此这般之后,大多数人还是输了,但也有一些幸运儿竟然赢了。但是在后人看来,无论输赢,正是这些不愿按规矩出牌的理想主义气质的政治家及其追随者,才为人类历史增添了些许醒目之光彩。否则,一部二十四史,何其单调、郁闷也!
何为传奇,何为悲剧,何为壮士,何为诗意?凡能感人心者正不足以成败论之。正是那些面临定数,面对必然,仍然心有所不服,慨然前出,奋力一搏,无论成败,以舒己愿者,方可在人类心灵史上留下至深印迹。
燕太子说出自己的计划后又强调:“惟壮士可担此任!” 荆轲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仅生逢其时,而且得人,有人欣赏、信任他,愿委之以重任。
荆轲迟疑良久,仍自谦辞让:“这可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在下能力有限,实不堪如此大任。”直到“太子前顿首,固请勿让,然后许诺。”实际上,无论是荆轲的向来之志,还是田光所做的铺垫,荆轲都不会真正拒绝。之所以如此,正如孔明上演刘备三顾的故事一样,不过是要测试太子的诚意,以及对自己的尊敬程度。这并非小伎俩,对士人来说很重要。此小插曲事关士人判明对方是否真正认可自己,自己是否值得“为知己者死”之大关节。
荆轲答应后,太子丹即厚遇之:将他当上卿对待,将他送到最好的地方住下,太子每天还要登门问寒问暖。每天的伙食标准是“太牢”——牛、羊、猪俱全。间或又有奇珍异宝相送,出门则有宝车美女相伴,荆轲的日子过得直如神仙一般。
如此这般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太子丹不见荆轲有所动静。其时,秦兵已进至燕之南界,太子恐惧,于是找到荆轲:“秦兵不日即可渡过易水,到那时我就是想好好伺候您,恐怕也不行了。”荆轲答曰:“不是我不愿行动,手上没有值钱东西,拿什么取信秦王呢?如果我能拿到您收留的秦将樊于期的脑袋,再加上燕国肥沃之地督亢的版图,便有可能打动秦王。”太子丹说:“樊将军本投奔我而来,我不能如此对待将军。你还是另想辙吧。”
荆轲知道太子不忍伤害樊将军,于是主动拜访樊于期。
“秦国待将军可谓不薄啊,杀了您的父母和整个宗族,现在听说又悬赏黄金千斤拿您的人头呢。”
“我早已愤恨之极,只是无计可施啊!”
“我这里有一招,既可解燕国之围,又可替您报仇,未知意下如何?”
“此话怎讲?”
“我若能拿您的脑袋去见秦王,必能取信于秦王。到时我便可手刃秦王,您的心头之恨,燕国的心腹之患也就全了了。”
于是,樊于期自刎,轲竟得樊首。
荆轲能设计出可行的接近秦王的方法,足见其谋略之智。他成功地拿到了樊于期的首级,说明他精准地了解樊于期的内心世界。更让人惊心者,他居然能毫无心理障碍地当面劝人自杀。这样的心理素质,理智、冷静得让人发抖,是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但这也正是一个职业杀手所应具备的东西,是这个职业对其从事人员的基本要求。
太子丹以百金征得天下名匕——“徐夫人”,以剧毒药染之。又征得燕国勇士秦舞阳,以佐荆轲。此人年仅十三即有杀人前科,人见之目不敢视,可见其凶。这是太子丹为荆轲做的准备工作,但荆轲仍以为未善。他又约了一个远方同伴,等待其同行。可是,太子仍不见动静,于是急了,怕荆轲变卦,就催他:“剩下的日子已不多了,先生您是否对此事真的上心?要不我先派秦舞阳去打探打探?”这下荆轲急了:“太子派秦舞阳有何用?无功而返有何趣!您以为孤身刺秦是闹着玩儿的?我所以尚未出发,是因我还约了其他人同行。既然太子嫌迟,那我现在就动身!”
两位英雄临场犯浑,悲剧的种子在启幕前已种下。太子丹既然对荆轲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不仅当钦其密,亦当信其诚,故而何时出发,当悉听尊便,应当做到用人不疑。此时,他已完全没有了一个政治家的胆略与豪迈,简直就是一个马上要求兑现好处的小人。千钧一发之际,太子丹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荆轲前面的谋划均属上乘,看他劝樊于期自杀是何等的冷静。可此时,太子一言不当,他便沉不住气。一怒之下,轻率地更改计划,提前出发。少了个同伴,便大大增加了刺秦风险。此时两位英雄的做派,与其前期准备之周密相比,反差真是太大了。千虑一失,功败垂成,如何能不令后人慨叹!
毕竟,荆轲出发了。刺秦在道理上的难度,以及现实的准备情形,当事人与旁观者心里都很清楚。可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就赌一把吧!因此,太子与其身边人都身着孝衣为荆轲和秦舞阳送行,知道他们多半不能活着回来。一行来到易水边,朋友高渐离沧桑地击筑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豪迈地长啸和之,终不顾而去。
这就叫悲剧——知其不可而为之,它的行为打破了世俗的做事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过就歇手,甚至逃跑;而是另一种做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悲剧情境下的主人公最看重的不是世俗的经济得失核算原则,而是对行为背后的价值理念之坚守,以及不计成本地坚守此观念所体现出来的意志与胆略,其对旁观者的精神震撼力正在于斯。
至秦,荆轲以重金赂秦之重臣,终获亲近秦王之机。一日,秦王听说燕国派人前来纳贡,于是决定召见荆轲一行。咸阳宫内,荆轲捧樊于期首级于前,秦舞阳奉燕国版图于后,依次而进。快到秦王座前时,秦舞阳临场恐惧失态。荆轲立即圆场:“边地上来的蛮夷之人,没见过世面,请大王少怪。”于是,荆轲继续上前献图。地图展开,露出匕首。荆轲即用匕刺秦王,秦王立时躲开,荆轲在殿上环绕追杀秦王,秦王以剑自卫。最后,荆轲未能成功刺秦,而为秦王所杀。
燕王喜惧秦,令人杀太子丹,谢其首级于秦,以息秦怒,终被俘灭国。荆轲刺秦之第二年,秦终并天下。死里逃生的始皇帝大捕荆轲余党。高渐离隐姓埋名,当了一名酒保,终因击筑而名,始皇召见。知其乃荆轲余党,毁其目而留其击筑。高渐离趁便藏铅块于筑。一日,高在殿上击筑时,用铅块击始皇未中,被诛。
荆轲虽死可慰,他并不孤独。田处士、樊于期成全于前,高渐离继承于后。这是一个光彩、激动人心的壮士群体。
五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刺客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社会群体。对这个群体无论赞赏或指责,恐怕都嫌太过简单。需要的也许是深入了解其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反思他们究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如此这般后,我们对这个充满神秘感的特殊群体,才会有足够的理解能力。
如果说以部落、国家为单位的正面、大规模战争是社会人群间解决物质利益冲突最激烈、典型,公开,甚至“合法”的表现形式;刺客群体所从事的暗杀活动便是利益冲突群体解决纠纷的微型、隐蔽,多半也“不合法”(即既不为实力派所代表的官方所认可,也不为社会公众的“舆情”所认可)的补充形式,今人称之为“恐怖主义”。这种特殊行为往往发生在实力悬殊的矛盾双方之间,因而往往由其中实力较弱的一方所采用。暗杀行为之所以不为主流意见所认可,原因大概有二:其一,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似乎有悖于武德,可谓“胜之不武”。其二,其民间“私了”方式挑战了官方的合法权威。但是,任何社会,只要官方不能尽行正义(无论古今,正义的绝对实施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企及的神话。),便为民间“私了”冲突留下生存空间,有时,相对于官方解决机制,它甚至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形式。当然,雇凶夺命只是其极端形态。
一方面是矛盾双方确实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似乎非夺命不可;另一方面,这种冲突又发生于实力悬殊的双方之间,靠正面、公开的实力较量,弱者永无胜算。实力悬殊又想取胜,而且还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夺人之命。这样的难题非智、力、勇三全者所不能办。为满足此类社会性需求,社会上便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特殊的职业——官方治理系统之外,民间形成的代人以特殊方式为人解困的机制——古谓之“刺客”,今人则称为“职业杀手”。
习惯上,我们乐于将这些人称为武林高手,似乎他们只善于打打杀杀,似乎他们真的每个人都有绝杀功夫,其实不然。当时他们就有一个很合适的名称——“士”。“士”首先可以用来指称文人,比如像孔、孟这样的有特殊价值观念或曰“主义”的儒士,或是像张仪、苏秦之类,在价值观上并无一定的“主义”需要坚持,但确实又有“主意”,靠向诸侯国君们贡献权谋之“术”而谋生的文人。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也用来称呼刺客这样的武人。只要认真分析刺客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确实也属于“士”。刺客群体之属于“士”,其胜人之处远不止于其武术,而有更深的精神内涵。他们在对精神价值观念的忠诚上,往往比许多儒士做得还要好。
何为“士”?“士”乃春秋战国时代崛起的一个新的平民阶层,他们有卓越的或文或武的专业技能。由于没有贵族背景,因此他们只能凭自身的真本事吃饭;为了能找着饭碗,他们浪迹天涯,“人生在路上”乃其生活常态;由于确实有真本事,因此比较傲气。这是中国历史上自我生命意识最早觉醒,个体意识最强的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文人,比如自觉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孔、颜之徒,自觉自愿地向诸侯们出卖自己的知识、智慧,以换取尊荣的张义、苏秦之辈,当然也包括了从曹沫到荆轲这样的刺客群体。在追求自我实现,渴望社会认同,追求职业荣誉这一点上,刺客们表现出突出的独特精神面貌,乃“士”之杰者。
“士”,无论文士——儒,还是武士——侠,确实属于社会精英,他们或以文胜,或以武胜,其生命能力——体力、智智、意志等方面均优于社会平均水平。因此,从纯技术层面讲,我们不得不承认——刺客这一职业对人的身体与精神素质要求极高,健强的体魄,高超的搏杀技能,深谋远虑的智慧,单刀赴会的勇气,等等,这些都是侠客们普遍具有的综合素质。能具备如此全面素质的人,当然是“人杰”,是精英,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英雄。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专业技术人员”,刺客们不仅生存能力上属于精英,而且他们对于这一事实十分了然,十分自负。他们急于实现自我,迫切要求社会明确、高度地认可其价值。这种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一旦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他们就会反弹出怀才不遇的人生消极情绪,这种情绪反过来又更激起他们对知音——“知己者”的巨大心理需求。一旦遇到知音,他们就会对赏识者十分地依赖与忠诚,就会加倍地报答其知遇之恩。于是,“士”阶层便产生了其特殊的职业道德观念——“士为知己者死”。如果说,对于一般的士阶层,“士为知己者死”只是一种夸张性的表述,刺客们却忠实地践行了这一职业信条。所有的刺客均勇于为知己者而死,大多数刺客为报知遇之恩而送命。
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自视甚高的职业刺客们是在为“知己者”而活着。未遇知音前,他们大多活得闷闷不乐。只有遇到知音,他们才活得活脱通透。但是,“知己者”的出场,一方面意味着刺客们人生高峰、职业顶点的到来——他们有事干了,可以发飙了;但另一方面,由于刺客的职业特征——他们干的都是取人性命的勾当,因此,在其人生价值实现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人生终点的到来——以命换命,以命相许。这正是刺客们的职业特征,是其命运的必然结局,因而这就是一个悲剧群体。
太史公笔下的刺客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确实遇到了知音。那不只是一个有刺客的时代,更重要者,那还是一个刺客能得到欣赏的时代。刺客们虽然最后大多都送了命,但他们所看重的价值观念最终得到社会认可,因而他们觉得自己死有所值,心灵并不孤寂。这大概正是从春秋到战国,刺客群体代有传人的原因。
赵襄子之于豫让,聂荣之于聂政,均可谓知音。没有这样的知音,这些英雄们亦难成其伟业。荆轲的知音群体中首先有太子丹。面临强秦压境,太子丹若认命认势,荆轲便只好待业至死。正是身处弱势而不认命的这股子倔强劲,才使得他与荆轲聚在一起。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面临秦统一六国大势不服输,总想知其不可而为之地赌一把。正是这种心劲与气质,使他有了理想主义色彩,区别于乃父所代表的绝大多数实现主义政客,在这一点上,他与刺客们实为同调,均是具有悲剧气质的人物。田光亦荆轲的知音。他首先在市井间认出了荆轲乃非常之人。田光虽无剑术,却有侠骨。他很看重太子丹对他的知遇之恩。当他认定自己无法出面为太子解危时,便向主人推荐了荆轲。更壮烈者,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为不因自己而泄密,也为了激励荆轲完成大业,他选择了自尽,其壮烈在性质上并不亚于荆轲的刺秦表演。凡能为一种观念,一种职责而主动舍身者,即为豪杰,即为侠客。荆轲的最后一位知音便是高渐离。刺秦前,他们相饮、相歌于酒肆,借酒乐言志抒怀,相知相惜直如钟子期与伯牙。荆轲壮志未酬身先死,留下了孤独难耐的高渐离。于是,他要继承太子丹与荆轲之遗志,为他们共同的事业继续奋斗,决定再与命运、强秦一搏。高渐离没有强健的体魄与专门的搏杀技能,根本作不了刺客;他甚连一般人都不如——已被始皇帝毁了双眼。可即便如此,高渐离还是毅然决然地出手了,反击了。是什么促使他这么做呢?是面对强秦而不服输的那股子倔强,是要报答荆轲相知的那种温情,是坚守心中信念的那份忠诚。他当然也输了,那是一定的;可即便如此,他总算酣畅淋漓地发泄了自己对强秦的不满,做了自己心中最想做的事情,为自己的朋友尽了力,既没委屈自己,也未对不起别人。这样壮怀激烈地死去,比起苟且、孤单独地活着,要舒坦多了。
世人所主动失命者,无非是为了钱。若非重金之诱,决无人玩儿命。一般的职业杀手是现实主义者,其行为仍遵循市场规则——唯利是图。诚然,他们也为其雇主解决难题,但是,他们行为的底线是在经济上要划得来,要得大于失。他们最看重的是利。正因如此,他们绝不会不要命地去夺人之命。从世俗的意义上讲,太史公笔下的这群刺客简直匪夷所思——一群不要命的家伙。他们虽然身手不凡,却智商极低——不懂得爱惜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有“主义”的群体,支持其英勇壮烈行为的核心价值观念,便是一个“义”字。在这里,“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公道、正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职业应当——“士为知己者死”和“知恩图报”。由于他们把“义”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职业灵魂,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些。只要有人赏识,为人舍命在所不辞。为了自己所看重的道德理念,他们能豪迈地捐弃世人最难割舍的生命。在回报自己的知音时,就可以不计成本,以命搏命,以命相许。他们是为了一种道德信念、职业荣誉而战。知恩图报是他们的行为动力与准则,他们往往做得比这更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直至“士为知己者死”。正是在此意义上,不能将他们与一般的职业杀手相提并论。
某种意义上说,刺客与其雇主,或“知己者”之间也是一笔交易。他人恩遇于前,刺客报恩于后。因此,只要有人找上门来,刺客们对对方的意图,以及这笔交易的成本了然于心。但是,刺客们所最看重的并不是世人所以为重的性命与金钱,而是自我实现,是其德、能被他人明确、高度地认可。他们所追求的,是将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一个行家,一个真正识货的人。一旦遇到这样一位“知己者”充分认可了他们的能耐与德性,刺客们就会爽快地为对方提供这个世界上最忠实、含金量最高的服务。因为这些刺客们一旦接了单,便将自己的全部,包括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身家性命抵押了出去。这是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的服务。正是这种极端忠诚的职业操守——忠于职责,知恩图报,舍生取义的精神追求,将他们与一般的武士、侠客区别开来。其卓越的生命能力与忠贞、勇猛的牺牲精神,使得他们在中国人的精神史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突出的位置。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基本上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事业,因此,他们也就成了恰当的悲剧主角,成了悲剧英雄,因为他们虽然代表正义,却又命运不济。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历史上缺少悲剧精神,其实不然。太史公笔下的刺客们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们所上演的一幕幕孤胆搏命、舍生取义传奇,便是中国人英雄主义精神和悲剧气质的典型表现,要寻找中国人悲剧精神、英雄主义的源头,就需要我们重温刺客传奇。太史公于在《史记 刺客列传》中评曰“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正是注意到了刺客群体的精神价值。
这是一个享乐主义与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二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享乐主义极其享受之能事;但是,当享受的欲望一旦受阻,人们便马上变成了犬儒主义——任何委屈都能受,什么原则也不想坚持,因为害怕因坚持原则而有所损失。
这是一个不但自己没有信仰,缺乏奉献精神,而且怀疑他人的奉献行为,对他人的奉献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的时代。这是一个用搞笑、戏说消解一切价值信仰,让自己成为一堆只会傻笑的行尸走肉的时代。
一个没有侠客出场的时代味同嚼蜡,一个没能力欣赏侠客精神的国度,更显其卑微。
在一个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国度,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们注定是孤寂的。他们的悲剧并不在于其壮志未酬,而在于他们死了也没人喝彩,在后代子孙那里,只能得到一个“傻瓜”的恶谥。在此意义上说中国人没有悲剧意识,欣赏不了英雄,也不能算错。
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