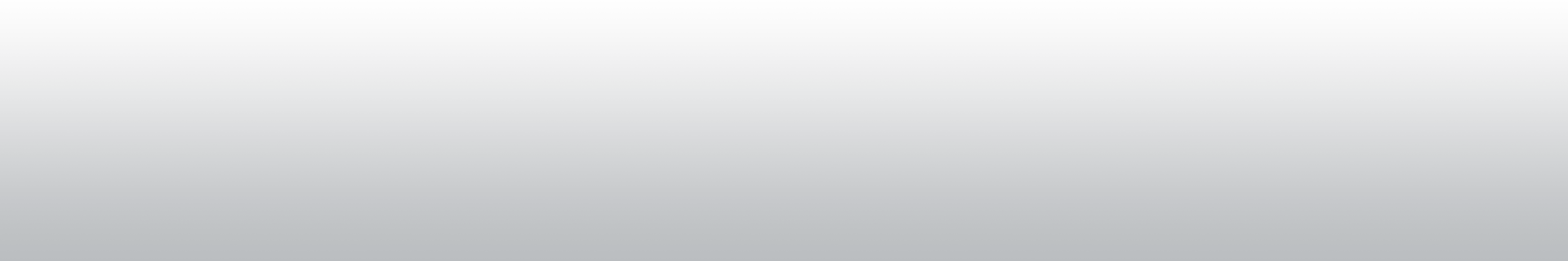仲牧先生印象
薛富兴
记得是1986年秋,我刚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同门师兄封孝伦知道我将来要到云南工作,就告诉我:“你们云南的赵仲牧先生可是个有学问的人,你以后到了云南,一定要去拜访他。”
大概是四年以后,我到云南楚雄师专中文系就职后,获得一个到昆明开会的机会。会议期间,我便去专门拜访仰慕已久的赵先生。
门铃响过,先生开门探视。我自报家门后,先生竟然说:“北京、上海,甚至海外的著名学者每到昆明,都要来拜访我,你这个小伙子怎么到现在才来啊?”我立时大窘,未能赞一辞。话虽如此,先生还是很热情地把我让进屋内。后来知道,先生喜欢开玩笑,此一戏语正足为先生的卓然个性风采传神。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此次会面所谈论的具体内容,现已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多数时间是先生高谈阔论,我洗耳恭听,听得很是过瘾。方知当年师兄之赞赏先生,诚非虚誉。其时,我硕士毕业未久,没见过任何大人物。第一次见先生,自然拘谨;但此次拜访并不算失败,有一细节为证。我大概是下午两、三点时去拜访先生,谈了很长时间,两人都很兴奋。突然,我们都闻到一股焦味。此时,先生才想起:原来他自己还没吃午饭。我进门后,他谈得一时兴起,竟忘了自己正在煮饭。初次拜访,不知道先生的起居节奏,现在才发现先生尚未用餐,我很是不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先生却很爽朗地安慰我:“没事,这说明我们俩谈得挺投机!”日后每忆起此情景,不禁感慨:先生是真正的书生,他是那种一驰入思想的境域,便真能高兴得忘了吃饭的人。首次拜访便如此唐突,却也略感安慰:至少,与先生交谈,我能提起他的雅兴。我早有所闻:其实,先生亦极为矜持,话不投机半句多。他若心里不高兴,是不会给你半点面子的。现在结果能如此,我便十二分地满意了。我知道,这正是日后与先生持续交往的重要基础。
真正得以较多地了解先生,还是在1997年我读博士毕业,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工作之后。
我当研究生,无论是读硕士,还是读博士,学的都是文艺学。自己虽爱好美学,然哲学理论修养方面极为欠缺,特别是西方哲学。先生于此则造诣尤深。从1997年秋至1998年夏,教书之余,我与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硕士生们一起听先生的课。上学期,听的是“符号学与符号美学”,下学期听的是“西方美学”。现在,我手里保存的听课笔记便成为曾与先生结缘的珍贵信物了。
出于对先生的真心爱戴与关心,中文系研究生们上课,节奏常依先生。记得上午的课是九点钟开始。每次上课,先生从容却又极准时地来到教室。从容地坐下,从容地掏出烟,先点上一支,吞云吐雾,细细品味一番。轻声细语中,课开始了。没有高亢的声调,没有激情的渲染,先生如春风化雨般地将学生们带入一个由广阔的知识视野、厚重的文化积淀、缜密的思维过程和精准的语言表达所开出的一片思想乐园,这是一种由阿波罗日神所营造的宁静、明朗、深邃之境。
我自己从中学到大学,所接受的都是极为正统的理论教育,读研期间虽也接触过一些西方美学、哲学理论,然均浏览而已,并未自觉、系统地用功。听赵先生讲分析哲学、现象学理论,开始的一两周,简直是一头雾水,因先生所讲者与自己的日常经验、曾经接受过的理论大为不类。所幸,先生最擅诲人。他能将艰深的哲学理论剥笋般层层析出,能为你回溯、还原出每种理论形成的思维过程,让你从理论源头上过程性、参与性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新观念。在先生的引领下,你也开始用别一种眼光看世界。不知不觉中,你也能悟出日常经验之浅,正统理念之弊,也能真切感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成果精彩之处;不知不觉中,这个世界好象变了,自己好象也变了,开始能体验到在抽象的哲思王国中心驰神往的乐趣,而不以之为苦为艰;不知不觉中,自己也培养起深疑与精辨的意识与能力,自觉地以之为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甚至是文人必须担当的庄严文化使命。这正是先生传播哲学的无量功德,正是思想家重铸人心的伟大精神力量。
大概是在1999年,先生应邀到云南蒙自师专讲学,我有幸得侍其左右,也就有了更好的与先生单独交谈的机会。蒙自师专的招待真是太热情了,不胜酒力的我,几乎天天头脑昏昏。记得有一次,晚饭后,我头重脚轻地陪先生出去散步。走了一圈,回到屋内,我仍处于高度亢奋状态。于是,我与先生对坐于床,半醉半醒地与先生交谈。当时我说了什么,现在已记不确。现在只忆得先生陡然为之改容,两行清泪簌簌的流下来:“小薛,你怎么能这样!一方面说赵老师,我要听你的课;另一方面又公然宣布我不信你这一套!”
先生一生嫁给与思想与学问,心无旁骛,全力精雕细刻自己的理论,视学术建树为安身立命之本。我却年轻气盛,借着酒劲,粗鲁地冲撞先生,引先生伤心。至今想起,深以为罪。
说真的,先生的魅力也真是太大了,凡有幸得承先生耳提面命者,无一不服鹰拜倒于门下,我自己亦如此。当时我正博士刚毕业,自我感觉良好。有时难免作如是想:“这也真是太可怕了,难道就这样轻易地被先生俘虏了去?难道就这样一直生活于先生的笼罩之下?”现在回想起来,不轻易服人的想法亦属自然,然直接向先生表白则纯属多余,至少,可以表达得委婉一些。谁知在酒的怂恿,我竟将此念向先生和盘托出,先生焉得不伤心?真是愚不可及。随年龄的增长,自己理解人的能力也增强了。我现在终于明白,要是换了我,大概也不会高兴。
先生上课十分投入。每次讲课,就其斯条慢理的表述风格推想,先生其实是在回溯自己的整个推理过程。课堂教学用的虽是口语,然遣词用语上从不肯有一丝粗疏,这样的一堂课下来,可想见其用神费脑程度。不仅如此,或要回答学生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或是先生自己讲得一时兴起,忘了时间,超额授课,往往有之。每次课后我能明显感受到:由于用力过猛,先生实很疲惫。
先生生性谨严,勤于思考,慎于著述。其一生的学术思想创获,大多即兴发布于课堂。作为先生的学生,同学们一方面为自己幸得亲接其馨咳为荣;另一方面,又每每以如此精论只施之于如此有限空间与人数,未得广布天下为憾。
刚调入中文系,系主任段炳昌先生让我充任科研秘书,有时及于研究生排课之事。我发现:一方面先生上课十分辛苦,无数精妙之思有待于整理;另一方面,每学期都有先生的课,有时不只一门。记得有一次,利用下课送先生回家之机,我当面向先生建言:少上些课,主要精力当用于整理学生们的上课笔记。不料此议深为先生所不取,当时我很纳闷,后来终于明白:还是我错了。
对我们来说,上课与写文章是两码事,似乎发表文章更重要;对先生则不然。没课的大部分时间,先生在思考、精磨着自己的精神成果。一旦有获,他便急需表达自己的思想,需要交流的对象,需要马上得到来自学生们的共鸣。对我们来说,读书、写作之余,有太多的事务足以分心,日叹其忙;对先生来说,独居一室,读书、思考之余,环堵孑然。他不找学生们交流,又去哪儿表达其积极的思想收获,排遣其消极的人生体验呢?先生在精神王国独行至远至深,一旦有获,他便急欲表达之、倾诉之,课堂与学生就成了他精神需求中最重要的部分。只要他活着,只要他还在思考,只要他思有所得,他就需要当下的直接交流。他可以累倒在讲台上,但他不能没有讲台与学生。因为,思想与传播思想是他此生之唯一。他太看重自己的思想成果,精神上太孤独了,因此,他对精神交流的渴望也就远比我们更为强烈。
先生是为书、为知识、为学问才投胎此世的。所以,这辈子他真的终贞不渝地嫁给了满架的书册,一生与之厮守如夫妻,谐和如琴瑟。最终臻于学究天人,思通古今,智融中外之境。
先生是为思想与智慧才游历此世的。所以,他来这个世界,并未遵“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通例,而是超逸、优雅地作了一个芸芸众生的旁观者。他以犀利的目光洞悉世界之本体与表象,又以会心的微笑观照世人之悲欢离合。先生以觉悟此世为业,今已得此大乐矣。
弟子们每以常情惜先生:先生至苦,先生至单调。其实,古往今来,得缘而历游此世者,何止万千,谁又是活得最完满的人?能从事自己所擅长与喜爱者,即为有福,先生则是大福之人。
一芥书生,以世俗观之,百无一用。然书生立世,其价值正在开拓精神空间。先生日日所游历、体验者,乃至广、至深、至精、至恒之境界,无有憾矣。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无论贵贱、智愚、顺逆、贤不屑,只此一遭;然书生如先生者,则大为不类,他是三世长存之人。他体验了今生的喜怒哀乐,此其与人所同者。通过阅读,他明白了自己尚未投胎之过去;通过讲授与写作,其思想与智慧足以影响来人。“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先生之出于滇云,乃滇云之幸。云南地处偏隅,山河阻隔,远离学术文化中心。幸有先生,众弟子乃可睹学问思想之高境。
先生之生于滇云,又先生之幸。众弟子凡得先生一言之教者,对先生无不终生敬爱。先生授课,学生奉其早餐;先生居室,学生清理之。课上弟子中,时有毕业多年,返而再听者。询其故则曰:先生之课,每轮均有新创。
我于2001年离开昆明。蒙故友不弃,获赠《赵仲牧文集》一册。哲人已逝,悲情堵心。明窗一编在,文思劢后人。
先生之学翰海,先生之志云霓,先生之业永光。其学其识,其德其业,足为滇云冠冕,儒林传奇,先生可含笑于地下矣。
先生之学,自有其众多高足为之整理,为之弘扬。今仅记数则私人性回忆于上,寄托我对先生之思。
2007-6-2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