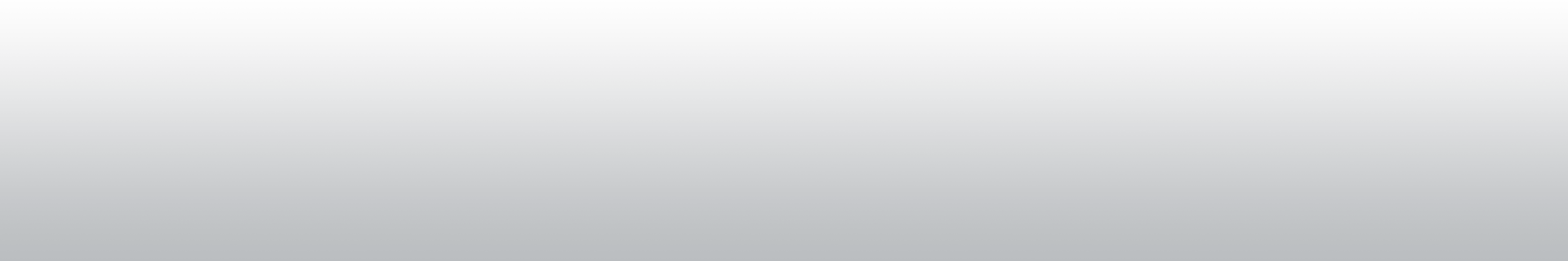色 谈
薛富兴
每个词都是一个故事。
──陆谷孙先生如是说
字典,人们总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向它表示应有的谦虚,虽然它从来就拥有最多的秘密。
“啪──”,因我的粗心,一本字典重重地摔了个跟斗,平躺在地上。
捡拾时,目光无意间落在打开的一页:
色 色彩。
人的表情。
妇女的美貌,如“六宫粉黛无颜色”。(白居易《长恨歌》)
有趣,一个本来泛指一切色彩的概念为什么会被女性所专有了呢?且看老外怎么说。兴冲冲翻开一本不算小的老外自己编的字典,一路盯过来,“......脸色,一种健康的玫瑰色或羞红。”用玫瑰来比喻女性之美在西方已是陈词滥调,看来马上就要有一样的灵感了,......然而最后还是擦肩而过。扫兴,真是死不开窍的老外。看来我不得不把这视为东智慧的又一象征了。
我折服于第一次将“色”与女性之美联系起来的先人。他是审美才子,一个天生的诗人和情种。他把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我相信色彩感是人类美感的源头)作为礼物慷慨地奉送给他的情人,反过来又用他的情人来描绘这整个世界。我相信这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诗,我们理当封他为华夏第一位桂冠诗人,而不是什么屈原。
“食色,性也”,告子又如是说。
这是一位哲人对人性的严肃思考,这里的“性”是人的本性、本能,而“色”显然成了与食欲相提并论的性欲、情欲的代名词,诗意荡然无存。
“始作俑者,其无后矣”。不管告子是否为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色”的第一人,我还是要诅咒他。
另一位哲人的话在我耳边响起: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出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多的思想”。
饶了告子吧,为他的坦诚。
别忘了今人的发明,当我们信手拈来一串诸如“女色”、“色情”、“桃色新闻”、“色胆包天”、“色迷迷”、“色鬼”、“色狼”......时,其中有几个能让人联想到初恋情人们的凝神,又有几个可以表达两性间超越肉欲的情感依恋?没有,有的只是一堆本能的赤裸裸展览而已。
“色”已经走过一段由“妇女美丽的容貌”到“女人”再到“情欲及其满足”的过程,最后径至于女性及其容貌成了情欲的代名词。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女性?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毕竟,这个世界只由这两种人构成,又不能不共戴天,贬损了其中的一半,另一半恐怕也会失去灵性。
一代魏晋名流绝倒多少后人。他们自己风流倜傥又喜欢对别人评头品足。这些选美大师们的口味甚高,似乎很少提及胸围和肱肌,而更重视风度气韵。抽一条“濯濯如春月柳”,你以为属于哪位建康(东晋都城,今南京)小姐,很遗憾你错了,这是给一位先生的评语。头号美男子卫�有一次被一群热情的追星妇人围了个水泄不通,结果“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 留下段“看杀卫�”的传奇。我不知道这位弱不禁看的卫�先生在今天的选美比赛中是否能入围。
魏晋名流之所以不同凡响,还因为他们只在大老爷儿们自己的圈内选美,他们大胆地倾吐七尺须眉间相互痴迷和依恋的温柔情怀。嵇康与吕安相好,每念及吕安往往转辗反侧,夜不成寐,最后不得不夜半驾车前往,互诉一番衷肠后才能了却一段心思。同性间友谊至此,不能不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其实我冤枉了古人,女性有时一不小心也会进入他们的眼帘:“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这是魏晋选美宝鉴,或云魏晋男儿相思录《世说新语》中的一句名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此前那么超逸玄远的口味为什么一到了女性这里,马上就降了一半。其实,对女性容貌身体的欣赏是十分正常的,但事实好像又不止于此:
“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天下相仿效......惠帝元康中,贵游弟子相与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晋书 王衍传》)
当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来临之时,东方古国也迈进了封建社会的末季。当西方人以惊喜的目光发现了,并大胆地在绘画中表现人体美之时,东方迎来了叙事文学的黄金时代,而艳情小说则是当时叙事文学中不可轻觑的一支生力军。这些杰作都出自富有文化素养的谦谦君子之手,他们如窃贼般戴上一副笔名的面具,用同一枝写字作画的笔来创造这种新“文学”。他们编一个冤大头来当自己的替身,自己想当色鬼就把别人都写成荡妇,以欣赏的情调在本能满足的大规模展览中获得意淫的快感。
仅止把这一奇观解释为对数千年封建礼教束缚的变态反叛是不够的,虽然这也是事实的一部分。它是一本供状:在这些主角(其实是作者)心目中,两性间的关系,除本能的发泄外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在一个男性尚扮演着主角的社会里,男性们的女性观,男性对女性生命的理解层次,也就是男性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层次,两性关系又是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两性关系的层次同时也是人类一代文明的标尺。
先把对方当成了动物,然后自己就真得成了一头畜生。
其实在整个古代,中西方男人的女性观更多的是英雄所见略同。本能是双方都有的本能,为什么独独要用女性(即使仅仅是其容貌)来指称这一本能呢?
就在东方的男子汉们封自己为这个世界的主人,而把女性仅仅当作自己满足生理欲望的工具,甚至这种欲望的代名词时,异邦的绅士们也编织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故事。据说,上帝是先造了男人亚当,然后又从他的身上抽出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夏娃,而不是刚好相反。其实这个故事并不像它的作者们所宣布的那么早,它大约发生在男人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对女王们的宫廷政变,为江山坐得稳当些,深感需要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伟大革命以安抚天下之后。
胜利了的男人们仍是群怪物,他们一方面把女人说成是引诱男人堕落的祸水,撒旦的同谋(海伦和妲己正是从极左和极右两个方向说明女性这种毁灭性邪恶力量的原型);另一方面由于上帝的捉弄(我是说由于本能的驱动),他们又勤快非常、绞尽脑汁地写出连篇累牍的诗篇去讨好女人,我真不敢想象抽去这些大老爷儿们奉献给女人们的拍马屁之作后人类艺术殿堂的情形。
真难为东西方哲人们以惊人相似的智慧都想到了蛇这种神秘的生灵。比起伊甸园里的那条来,东方的已作了许夫人的白蛇似乎更有深意,它微妙地凝结了男子汉们对女性的所有复杂感情。
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