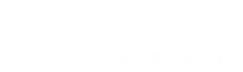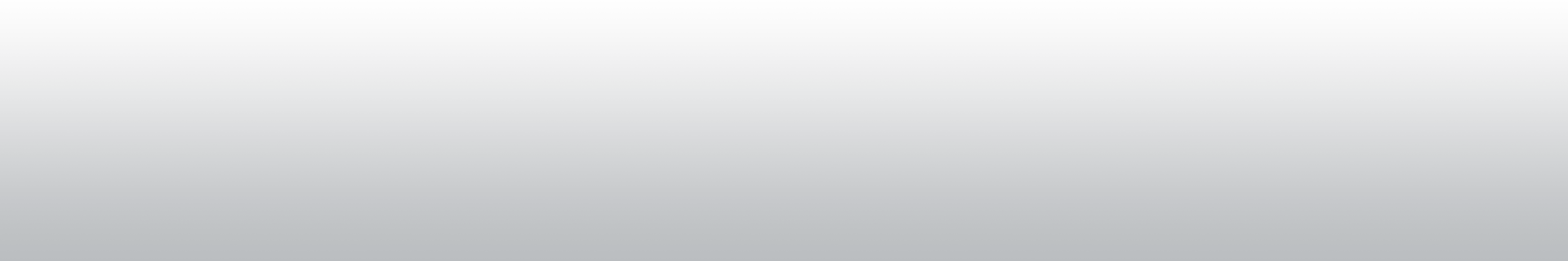青年与中年
薛富兴
感谢陈独秀们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以此为平台唤醒民智,为现代中国塑造了一代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终使老大帝国再次焕发青春。“新青年”因此也就成了国人讨论青年问题的便当话题。
陈独秀们是对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希望都在其青年,一个民族的潜质与能量取决定其青年人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一个民族不断提出和思考青年问题,说明他尚未进入老境,因为他还有进步的欲望。
最近,我从朋友那里得到这样一幅关于当代中国青年的素描:当下的青年人已不再有激情、抱负与社会责任感,一个个过早地变成了现实主义者,没有了全社会心目中所期望的那种青年人应有的状态。甚至,当下的中国也没有了少年,现在的小孩子们在青春类影视、网络传媒的影响下,过早地青年化了。
一个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少年和青年的国家,怎么展望自己的未来?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可是谁让他们变成如此模样?
青年自有青年的特征,就青年人在生活方式上所拥有的独立特行时尚面孔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一种“青年文化”,这正是当代文化研究者的思路;但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形是:青年又是一个心理上谋求独立,实际上尚不能“大丈夫自树立”的特殊群体。二十岁左右的年青人处于学习或创业之初,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他们都被认为正处于一个工作经验不足、技能尚不熟练,思想尚不成熟的阶段,是一个经济条件较差,社会地位尚低,正需要向中年人学习的阶段。因此,就青年人的现实生存能力和在社会整体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而言,“青年文化”充其量只是一种“亚文化”。
是谁真正掌握着青年人的命运?经过20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然成功地走出传统的老年型社会,而进入到一个中年人主政的时代。无论是社会物质资源的掌握、制度安排的权力,还是观念表达的机会,不是青年人,而是中年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强力集团。因此,青年人的命运正掌握在其父辈手里,青年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年群体的素质、自省与努力。
我们确实有一个举世闻名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当代中国的父母们已将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他们把让孩子们在未来社会获得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设定为教育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把人生竞技场前提到了幼儿教育阶段,并贯彻到中小学。他们创造出的当代教育格言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他们以素质教育的名义让刚进幼儿园的孩子们就不停地进行各种艺术技能培训,应试则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全部目的。中小学生每天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被拴到了校内的课本、试卷,及课外的学业辅导和艺术技能培训上,不要说他们缺少自由娱乐、自由学习、自由实践的时间,许多人甚至不能保证一个正常人所需要的足够睡眠!原以为到了大学,学生们终可以告别应试,自由且快乐地学习了。结果发现:大学虽自由,但大学生们仍忙于考取各式专业等级证书。十多年的集中营式的高强度被动学习之后,许多理当思想最为活跃,创造力最为旺盛的大学生们,对新知与卓思已然没有了热情,对学习与自主思考已然失去了兴趣。由于中小学阶段的心力透支,他们已然提前进入心理能量的衰减期,更多地是要考虑将来的生计了。
也许有一天,当你们的孩子已不再是孩子,甚至不再年轻,他会很忧伤地对你们说:“爸爸、妈妈,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年轻过,我甚至没有过自己的人生!在我最想玩儿的时候没时间玩儿,我虽然为你们争足了面子,可我自己并不快乐。现在我虽然挣得不少,可我很无聊。活到今天,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想法,一切都是照你们规划好的路线走过来的!”你能让他重来一次吗?
合理、完善的教育应当以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个性、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丰富学生的生活情趣、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为宗旨。完全依附于考试的教育本质上说不是教育,充其量只是技能培训,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灵魂。教育制度的缺陷反应了教育理念的缺失,教育理念则根本上反映了一时代、一民族的人生哲学、战略眼光和文明境界。一种赤裸裸地只盯上成绩、技能、金钱等功利目标的教育所培养的青年人,既不可能有个人的人生幸福,也不可能有卓越的民族竞争力。作为个体,他们将是一些永远活得累,却找不着幸福感的可怜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永远只能从事一些最基本的生产和服务,不可能在当代人类文化的高端做出重要贡献。
某种意义上说,父母是孩子的上帝,中年人决定着青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未来命运。当下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正体现了当代中年群体的文明层次和人生境界,正考验着他们的社会良知与民族责任。整个中年群体正需要深刻反省。每个为人父母者都需要扪心自问:我的孩子是否真的得到了健康、全面的发展,我的孩子是否真的活得快乐、幸福?每个中年人都需要扪心自问:当我们思想成熟、精力充沛,有能力做点儿实事的时候,我们到底为青年人做了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先生当年所提出的“救救孩子”和“我们怎样做父亲”,在当代中国仍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谨以此纪念永远的“五四”。
2009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