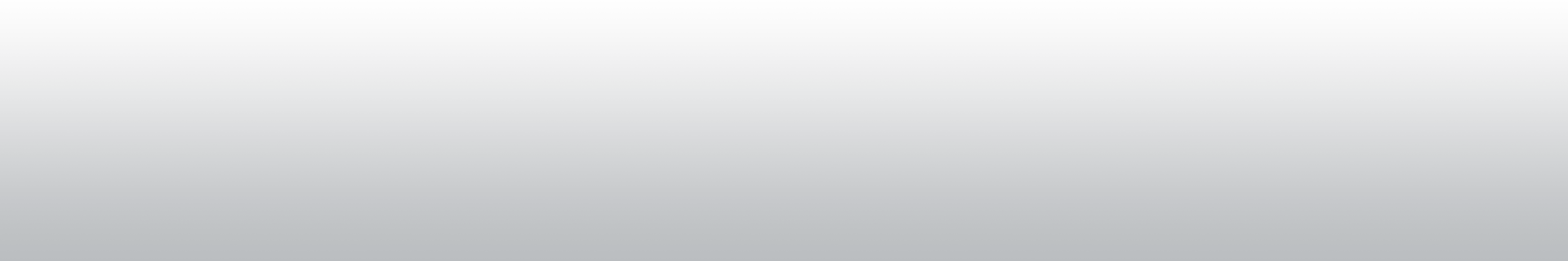沧海回家
高晖
读沧海的这些文字,特别是涉及到抒情的章节时,总能让我想起他的一幅照片。照片肯定拍摄于上个世纪80年代,像素、光线以及色彩都更接近现实,而且里面有种幽幽的抒情气息——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对这些东西都很敏感。照片的背景是一幅黑漆漆的山水画作,大约是他的毕业作品——我始终没有问沧海这些细节,沧海也不知道我看过这张照片。我要说的是,照片里面的沧海:漆黑的裤子、雪白的衬衣、浓密的头发,还有细细的腰身,这个沧海像一匹马,一匹心怀梦想的马。沧海的所有骨骼都微微收缩,皮下的肌肉张弛有度,沧海的面容内敛而孤傲、清癯而疏朗。总之,我们可以用俊朗、俊逸、潇洒、�丽等等这些词汇来修辞那个沧海。
当我看到沧海本人的时候,同样是上个世纪,但已是90年代中期,那时沧海常常能将自己喝醉。在我的印象里,沧海几乎都是和交通工具共同存在,并且一起沉醉,或是自行车,或是摩托车,大都是他驾驭着它们在南开大学校园里蜿蜒前行。其实,也就是90年代中后期的那些年,沧海,完成了自己做为艺术家的聚变,同时开始用文字记录关于绘画的感悟。沧海全身心地投入到书画研究和实践中——他几乎就是带着绘画的使命来到尘世的,每时每刻都竭力吸纳着与绘画有关的一切。沧海是个天生的画家。
我是因郭长虹先生而结识尹沧海先生,常常是我去南开看长虹,然后沧海几乎每次都会从某一特定的角落突然而至。于是,我们就开始谈话,然后喝酒,或者边喝边聊。沧海说话,大体分两个步骤,提出观点并随之进行论证。陈述观点时,沧海常常表情沉静、吐字精准,但一进入论证表述阶段,由于乡音较重,加之伴有慷慨激昂状,我总是很难全部听清,但这不妨碍我们的交流——在我和沧海的交流中,常常介入自己的主观推测。边喝边聊时,总会在某一刻,大家先是大呼小叫、既而沉默无语,一般都是这样——我们于是都醉了——当时的确总是这样。谈话的内容,现在大多已经忘记,不过肯定都是艺术范畴的东西。我们这些“60后”中有一小撮人几乎都是这样的经验:那些年月,常常是那样莫名的激愤、躁动、委屈,甚至是绝望——真的,我们的身体器官还不习惯这样的世界,但那段时光也是与艺术本身无限接近的时光,尽管它和80年代中后期还有很大的差别。
进入21世纪的时候,沧海开始茁壮,细腰开始变粗,不过依旧敦实而灵动。在外形博大的同时,沧海内在的大家气象已经彰显,其中对书画的理论研究已走向纵深而开阔,文字也愈加自然、古拙、超迈。这时,沧海壮硕的体态压迫着原来的心脏,也已成为一个超负荷运转的人;不过,在灵魂深处,沧海依旧和那张照片一样,温情、羞涩还有内在的俊朗,只是外在的物象略显沉重罢了。可以断定,沧海的心脏与他那超重的肉身的关系,正如沧海本人同时代的关系,无疑都应该是紧张的——其实,对于后者,对于那些优异的艺术家几乎都是这样状况。我坚信,沧海完全有能力克制这些。但,我还是忍不住这样想: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沧海变得壮硕、蓬勃而超重?艺术本身,还是之外的东西?沧海的确不知道,我看到了他那张特别的照片。
沧海擅画人物、山水、花鸟、书法,而且,沧海的画作迄今无疑已显示出大气象。近年来,国内美术批评界论及沧海的书画,我大致可梳理如下:沧海作大幅山水气势恢宏;作人物、花鸟多见性情,笔墨精湛,韵味拙朴、崎峻、恬淡。其书法结体清奇、书为心画、清新俊逸、笔精墨妙、古雅出尘。对于中国画,我只是观者、读者,不敢妄言。但我觉得,其中“韵味拙朴、崎峻、恬淡”的画风,也符合沧海文章的体貌特征。
沧海迄今的文字,我几乎都看过,现有《复归与朴——写意花鸟要旨》、《沧海一粟》、《写生课》等三部文字比较集中的专著。去年秋天,我对沧海建议,修订一下《复归与朴——写意花鸟要旨》。于是,我将该书推荐给辽海出版社总编辑于景祥先生,很快就得到了赞同。当时,拟定由沧海将《复归与朴——写意花鸟要旨》原有章节进行修订,增加沧海新近的谈艺论文、随笔、序言、后记等分别重组成沧海拾贝、砚边拾零等两个部分,书名即为《沧海论画》。
还说沧海的文字。沧海的文字自然、古拙,熟悉沧海绘画的人,一眼就可以断定是他写出来的东西。沧海首先是文人,其次才是画家,这是我认定的顺序。其实,无论绘画、诗歌、散文还是论文——他们共同之处就是书写——在同一个画家(或作家)身上,总能发出相同的声音。那么,沧海的声音是什么呢?在这本书里,沧海用文字体悟出的探求、理性与情感,实际上还是从他内在生命本身的底座生发出来的东西——他之所以选择这些,是因为他需要它们。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沧海的艺术精神、文化传承以及日常状态,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读出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性情——当然,这些是都是属于无法传承的部分。画家在宣纸上泼洒的水墨痕迹与作者用文字表达的理性与情感的文字印迹有着令人诡异的统一,我的意思是说:尹沧海对山水花鸟的探寻、解读、阐释、领悟,所有这些,在历经思维、文字、书写的过滤后,最终都会自动地“滴”在敏锐而温情的宣纸上。也许,就是这些构成了画家尹沧海的全部;也正是这些,沧海发出了一个艺术家特有的声音。
看到沧海日记《从台北到太行》时,我再次想起沧海那张照片——里面有一段描述家乡和母亲的文字:
乡村还是如此静谧,太阳暖暖地照耀着我的村庄。家门口几株竹子在微风中摇曳,两只绵羊在悠闲地吃着草,院子周围被许多高高的树围绕着,有三两个鸟巢筑在上面。老母亲就端坐在门口晒太阳。这是我今年的第四次回家。母亲老了,偶尔脑子有些糊涂,有些以前熟悉的人她会不认识,但是我每次回家,她会很高兴。我拿出一些钱给她,母亲一直攥在手里,一个女同学问:老奶奶,够花吗?母亲说,够花,够花。母亲话很少。其实,我很想留下来一天陪陪母亲,奈何学生太多,晚上需要赶回县城。车开动了,母亲在车后面跟了几步,我赶忙叫司机停下……
每当沧海的内心归于平静的时候,总能听到那细微而灵动的声音。这时的沧海,总是内心温润、晴朗、凝重、纯真,肉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打开,像童年少年的身体一样敏锐,他可以听到微风的声响、土地的特别气息,还有自己血液流淌的声音。他的若干绘画正如他的若干文字一样——我觉得,其实这些年来,沧海始终在画同一幅画,那就是上面这些温润的文字所传达的画面:空灵、顿悟、剔透,还有难以摆脱的绝望,以及最后抵达的虚静。沧海“回家”的次数、密度、深度,决定着沧海绘画以及书写表达。这些,应该是沧海内心深处的根脉;也就是这些,形成了沧海那独特的、裹挟着现代精神的古典气质。
正如沧海的母亲,由于年迈,有些以前熟悉的人常常不记得了,但是,沧海每一次回家,她都会很高兴——并没有因为儿子外形的变化而选择遗忘。我们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母亲肯定都会认出他的儿子,也总会盼望着儿子的一次次回家。
2007年秋天,我和沧海连续在山上见面——九华山、千山。在千山第一个晚上,我、沧海、王晓宇挤在庙里的一面土炕上。凌晨时分,我自然被冰冷的山气冻醒,睁眼看到在月光下打坐的沧海:双目紧闭、面色红润、大汗淋漓……那一刻,我眼前的沧海和照片上那个沧海已经完全重叠。时间已经无法修订沧海——原来沧海心中早已存在一幅特殊的画卷,他的所有的文字甚至貌相都是这幅画的草稿。其实,沧海心中的山水早已不再是真山真水,而是被沧海过滤掉杂质、剔除了烟火气味的另种山水。此刻的沧海呢,已将对故乡的回望,提升为对精神家园的皈依。
高晖 作家、文学批评家。代表作:长篇小说《康家村纪事》、文学批评集《原始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