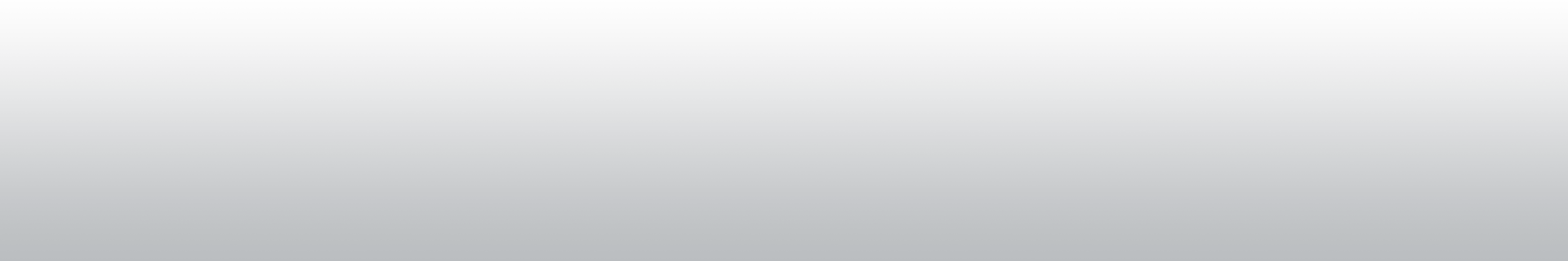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河上花图卷》是八大山人的代表作品之一,纸本,墨笔,纵47厘米,横1292.5厘米。全卷以荷花为主。画尾自赋《河上花歌》37行,赋后跋有:“蕙岩先生属画此卷。自丁丑五年以至六、七、八月荷叶荷花落成。戏作河上花歌仅二百余字呈正。”款署:“八大山人。”丁丑即1697年,可知此图为其72岁所作。拖尾另有清永瑆、近人徐世昌跋,卷中钤有近人徐世昌鉴藏印多方。徐世章先生在引首行书题“寒烟淡墨如见其人”。后几经辗转,捐献给天津博物馆。
八大山人,名朱耷,明太祖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江西南昌人。明亡后,落发为僧,后又蓄发,做过道士,晚年又还俗,用过雪个、个山、驴、驴屋等号,后取号八大山人,沿用到去世。从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看,八大山人早年的一些行为似有些神经质,然而他的“忽狂忽暗,隐约玩世”的心理,正是他胸中积郁的亡国苦痛的体现,这在他的画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他画的鸟、鸭和其他动物,眼睛部分特别夸张,有时候眼眶画为方形,眼睛多数是点在眼眶的上角,“白眼向人”,寄托着作者的悲愤与孤独。然而艺术最终是对灵魂的大慰藉,从大牢笼得大自在,这便是为什么对八大山人的艺术用得上“冷逸”二字的原因。“冷”当然是八大山人对来自社会、人生的感觉,这其中成就了八大山人特立独行的人格和寂然自守的孤抱;而“逸”则是八大山人对困境的心灵超越,这正铸炼了他艺术上卓尔不群的气质和清峻绝俗的笔墨。这两者的融合便是八大山人在美术史上所创造的不朽符号。
八大晚年的作品趋于一种返朴归真的风貌。他72岁时的这幅《河上花图卷》已不再是前期隐约玩世的情绪心态了,而是洋溢着如枯木逢春般生命活力,展现了八大山人精湛的笔墨与平和心态。此卷于清静、纯净,平淡中蓄真情。画到平淡天真处,方能真正体现出物我交融之气质。此种“真”与“平淡”又是画家人品、思想、秉性、才情之自然流露,而非平庸与庸俗的简单。禅宗讲“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坛经·般若品》),就写意画笔墨来说,是在无墨处求画理。往往是笔愈简而意愈周,愈丰富则愈虚淡、含蓄。中国写意画到八大山人,在笔墨运用上已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已能做到心与笔合,一点一画,隐迹立形,备遗不俗,如此清华之笔墨,皆在于发诸心意,是八大山人在特定的环境下精神的一种放逸方式。
《河上花图卷》与自赋《河上花歌》的诗作以及书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河上花图卷》开首数笔,写荷叶初展,荷花菡萏初成,再以数根饱满劲健的线条相连,错落有致,使画面顿生临风摇曳之态。接下来以苍润之笔墨写河沿、山壁及坡石,间以重墨勾草点苔,又以大笔蘸水以破墨法写淡墨荷叶并勾花隐露于叶间,使与引首浓重的茎、花、叶、以及壁间之坡石之苍润之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八大的用笔似由冷静转向纵横恣肆,挥毫入纸如云烟,写叶之重重,花之摇摇,茎之修修,墨之浓、淡、干、湿、焦、白,笔之疾、缓、顺、逆,无不用其极。又写河底坡石二块,略呈云头皴法,一呈斜三角,另一巨石顶天立地,呈倒斜三角状,坡底数笔淡墨苍润,线顺势而下,最近处几条重墨线错落穿插,倒三角形巨石左下一条墨线斜贯于两石中间,几块重墨构成的荷叶与两石之间以破墨写出的水墨韵章、重重叠叠之荷花荷叶略呈波折状,“C”字型构图中,间以波折线构图。中心空白处悠渺无尽的天空中似蕴含着无限的变化。
这块极具动感的倒斜三角巨石一直延伸到画面的极近处,坡石之上,以圆劲之中锋用笔与巨石呈反向勾勒出一株枯柳,自右上至左下,飘摇在这一方幽渺的空间里,背景以枯笔淡墨中侧锋相间自上而下迅疾扫出,由近极远,与河底数条有着抒情意味的平行线相交,构成平行线与垂直线相交的构图法,于平静中蕴含一派肃瑟与空寂之境。但是,这种短暂的沉静之后呈现于观众的却是在画家理性驾驭之下的更加冲撞之激越,它把观众的情绪引向最高潮。
画面向前延伸,一块大石突凸,极具体质感,石隙间又有莲叶与几枝莲茎,莲茎极重而莲叶极淡,在压迫下的空间与远处数块垒垒落落的坡石中间,莲叶苍郁挺拔,碧绿连天,整段画面充满了动荡与波动。在这一片肃条之氛围里,在这穷山剩水之间,在这荒芜的土坡与岩石之下虽不得不折腰,却依然花显叶葳,生意勃发。纵观前半卷,这实在是八大山人对老子所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老子.第二十八章》)之参透。“知其白,守其黑”指知阳而守阴,知刚而守柔,一切处于蓄势待发之状态,不用刻意为之,而是无处而不可,无处而不适,如流泉之注地,轻云之出岫,如烟生霞飞,雪飘霰落,了无定则。此卷最迷人处还在画面之空白,往往一块石头背后的空白,事物宛在浑然天地,寥廓宇宙之中。精妙的笔墨,纯发乎心灵。也是其抛弃一切我执 、法执的羁索之真正的大自在之体现。
如果说上半卷是写空谷无人,水流花开,那么后半卷则是写老僧枯尘,诸法空象。再往下看,那山石累累无尽的开阔处,犹残露着兰之芬,隐含着竹之节,卷尾的山石层叠中的高涧流泉,冰冷如铁,又作何喻意?是天性的绝境,还是生生不息的新生命的开始?下半卷的构图多以水平线与垂直线相交之构图,间以斜线,使画面在“空”、“寂”、“冷”、“静”中寓以动感,犹如一位粗服乱发的老僧,静静地内观在这山间河谷之中。
这又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宋代苏轼之诗句“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是啊,这也不由使人想起八大晚年的出家与返俗之辨,事实上,其晚年为僧或不为僧,他都是。彻底悟禅者,大地皆为蒲团,正不必在丛林;钟磐之声,依旧在心头缭绕,也不在佛堂。老境来临的时候,八大山人的心灵愈趋宁寂,平静,恬淡,他远离了生平所经历的劫难和心灵上的震恐,挂碍,颠倒梦想,具有了一颗真正的平常心。当一个人能以平常心对待一切色相的时候,那目之所见决不是奇谲怪诞的所在,唯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达致无心无待而与天地精神相往返的境界。卷尾所跋,颇能反映出山人与现实之心境,在题跋中,八大山人发出如此人生之感慨:“撑肠挂腹六十尺,炎凉尽作高冠戴”以及他晚年对平静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吁嗟世界蓬花里,还丹未?乐歌行,泉飞叠叠花循循。” 明清的文人画风,受董其昌的影响很大,八大山人的初期山水画和书法,也同样受到董其昌的影响,但他晚年的山水画则变董氏的秀逸平和为空寂冷逸。在书风上变赵之俊秀清雅为大开大阖,变赵之侧峰疏朗为中峰圆浑,变赵之连绵洒落为圆润空寂。
八大山人《河上花图卷》是其水墨写意花鸟画中难得的巨制。是他顺乎自然的心灵境域。感谢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为此所做的工作,并希望这幅画卷的出版能如和风拂煦之中的抽丝吐绿,给当代颇觉烦躁的艺林带来一抹春色。
尹沧海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