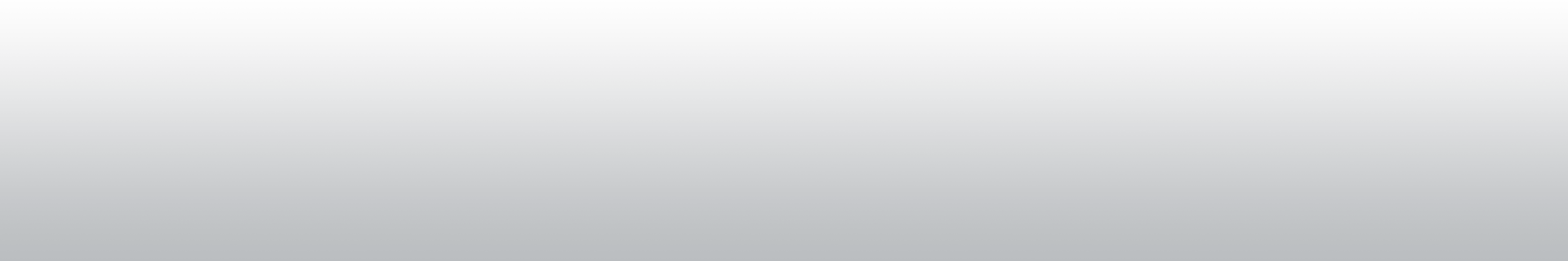梁斌先生和他的绘画
作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问世的中国文坛上的惊世力作——梁斌先生的《红旗谱》,在那个年代,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连同它的续篇《播火记》、《烽烟图》等,构成了一幅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变革的历史画卷,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不朽丰碑。说到《红旗谱》,不禁联想到我的少年时代。老家萧县是个画风极盛的地方,我自幼自然也是耳濡目染,陶醉其中。记得最早临摹的连环画之一便是《红旗谱》,也是由那时起知道了梁斌先生的名讳。因为一段时间,我临习《红旗谱》以至于到几乎完全能背临的程度。从故事情节到人物造型到构图笔法等等,往往闭上眼睛人物形象便如在目前。我生也晚,未得拜见梁斌先生,如今忆及,自是一段因缘。而接触梁斌先生的书画,则是在八十年代我在美院读书时,学校组织的一次画展参观。一进展厅,便被他那创变的新奇水墨话语所感动,他用自己的方式描绘着各种植物和山水,构筑成了属于自家墨象的特殊语境。
宋代是中国文人写意画的兴盛时期。皇家的支持,加之文人士大夫、僧侣处士以文事、哲理入画理,以体悟之心入画,对于客观之认识,偏向于象征与移情之作用。如苏东坡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文同的墨竹画法,米芾以蔗滓与纸筋所作的墨戏以及南宋梁楷、牧溪(法常)等人的艺术,都在求形外之意的画家之列。元代以后文人画的发展,使中国绘画由纯粹绘画,偏向于主观的象征性与移情作用之写意画,并且在绘画形式上有所谓的写胸中逸气,逸笔草草的概念形成,以及对“写竹还须八法通”式的书画同源之认定。文人画在意境的营造上,突出的表现为诗境和画境的融合。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相当大程度是以佛道思想为基础的,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以审美的态度追求天人合一,这便是诗画交融的哲学根基。在具体化历史进程中,随着文学、绘画的自律发展,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逐渐形成了具有典型特色的“以诗为魂”的写意画样式。在创作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是首先由王维实现的,而理论上的偶发与提倡则是苏轼。苏轼以后,文人画、文人写意画无论创作上还是理论上都已初具规模。明董其昌又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而 “行路”则可延伸为阅历与做人,乃至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
及至当代,从风雨飘摇,西学东渐的八十年代中叶,到提倡自然和谐与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今天,提倡写生与体验,以书画实现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某种责任感,一直是艺术家所追寻的为艺为文之道。著名理论家陈绶祥先生曾提出:“从黄河流域的故土中摔打学习,从中华故土中脱胎换骨”。这不禁让我联想起梁斌先生和他的书画。因为我们从梁斌先生的书画中,在感受到他作为文学家诗人在书画中体现出的历史的、社会的责任感的同时,还强烈的感受到他作为饱经沧桑的革命者的达观与浪漫主义情怀。
在梁斌先生的咏梅作品里,更多的不是表现梅花之表象,而是通过梅花所体现出来的气节来表现人的气骨丰神。《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云及:“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道出了花鸟画的托物言志与文学传统有关。《论语》中借松柏表达坚贞的人格;屈原的《离骚》以美人香草寄托诗人的高尚情操;而这种传统表现在花鸟画创作上,则是画家结合自然物象的艺术特点予以表现,花鸟画中的“梅”被喻为“四君子”之一,正是这种“喻兴”在写意花鸟画中的体现。好的写意花鸟画作品自然能引发观者的联想与想象,唤起人生的某种情思与审美体验。
梁斌先生的《梅为百花魁》纸本,纯以水墨而出。画面一株梅花老干自下而上,顶天立地。用笔不疾不徐,间以浓淡皴擦,或画斫断之枝于画面近中间部分,益使人多作联想,面斫断枝干又发枝发花,连同梅树上方的无数枝条,观之如万朵琼花齐放,枝干相互辉映,使人心逸神畅,而无病梅之弊。画面左中下方大面积空白,构图略成“C”字形,使得整幅画面愈发气韵流贯。从枝干到勾花再到构图皆用己意,风格凸显而又暗合规矩。画面左下方,又以楷入隶,以拙入巧,题云:“你画你的,我画我的,各有各法”。明人论笔墨云:“气有笔气、墨气、又有气势、气度、气机”。通观此帧,当意不仅在于笔墨,重在气度与胸襟也。
读梁斌先生的另一幅作品《香雪海》,仿佛使观赏者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之中。画面将老干节疤绘于画面中心,以新奇夸张的满构图凸显出漫天飞舞的梅花盛开之势。古人论画云:“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而反之亦然。梁斌先生此帧,虽画满树梅花,充满画面,但却让观者觉得清气满幅,勾花虚实相间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亦如黄宾虹先生所云:“密可走马”是也。新枝老干之中,弥漫着层层叠叠的梅花,又仿佛是无数个音符,在梁斌先生的指挥下演奏着生命的交响。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说:“绘画以形似,见于儿童临”。现当代画家齐白石也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主张“以神写形”的画,兴之所至,发诸毫端,包含着感情和兴会,是景物生命基调在造型中的显现,也是作者生命基调的寄托,具有丰富的内涵。
梁斌先生画墨荷,不仅有北宋周敦颐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之情境,更有梁斌先生自己赋予荷花的丰富的当代内涵。将自我融进祖国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大环境之中,去审视生命的价值。在不同环境中所表现出的“荷”之境界,无不彰显出梁斌将“我”融入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生存共欢乐的“大我”之中。
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不仅仅是指大自然中的自然。自西汉董仲舒以自然之道释儒家之“仁”、“礼”之后,于民族文化意识中,更是将以社稷为本位视为大自然之理,从而形成民族审美特性的主要标志。这一点在梁斌系列墨荷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例如,他在表现荷与自然的关系中,不仅有“朝露”、“雨露”、“艳阳天气”自然环境中的荷花,也有“战争”、“改革开放”等社会政治环境中的荷花。正如他自己所说,“昔日曾游泮水边,少年泮上走玉莲;白发做完南柯梦,改革开放又一程。”所以于各种环境中,他以荷喻己,其中不仅表现出生命与自然的和谐性,也寓意着“小我”与“大我”共生的融合性。正是这种审美意识,使《千年难忘白洋淀》、《西风叶》等作品,激荡着当年为民、为国与敌征战的豪情。难怪梁斌画荷,却题为“千年难忘白洋淀”,画“西风叶”却情不自禁的提笔写下“谁想当年征战事,安知老翁栽藕秧”,在《南柯梦改革开放》、《接天莲叶无穷碧》中,却能感受到他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的情志。
在梁斌先生的绘画作品中,我尤其喜爱其山水作品。黄胄先生称其为“革命的文人画”;叶毓中先生说:“文学家梁斌、画家梁斌是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缔造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家梁斌一起成长、一起辉煌的。确切讲,是革命家梁斌催生出文学家梁斌、画家梁斌的。识字的不全是文学家,会画的不全是画家,解读梁斌的书画作品,会给我们无尽的启迪。”用梁斌先生自己的话说:“你画你的,我画我的”。听其言,观其画,不能不令人想起石涛,石涛云:“搜尽奇峰打草稿”;亦云:“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之人不能一出头地也。”“我之为我,自有自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也?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苦瓜和尚画语录》)梁斌先生之画与石涛画论,诚异代知己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其对于绘画之法既应有在学的过程中的“益”,也应该认识到绘画的终极不是单纯的法的增益,而应该在法度完备的情况下“损之又损”,直至达到内心的纯粹表达,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坛经·行由品》“人得一以宁”(《老子》),所以“有法”“无法”只是在特定时空下对待创作的一种态度,如果能任乎自然而归乎朴之单纯,那么,就不会囿于“有法”或“无法”的执着。这也许就是作为文学家、画家的梁斌先生和他的作品应给于人们的启示吧。
画史有云“画须熟后熟”,第一个“熟”指熟练而后一个“熟”字。则这需要艺术家过人的天份与较高的艺术修养方能把握的尺度,梁斌先生能做到驾轻就熟,心无滞碍,亦不为法碍。金刚经云:“壁如伐喻”,正是指也。
我爱《狼牙山》中如钢铁铸就的高岩,和五座、六座乃至无数座有着正三角样坚固的群峰,乃至群峰罗列下殷红如血的柿子树。我爱《五十三年前进太行》中的曲折盘旋的山道和笔墨中生发的蓬勃之精神。我爱梁斌先生以革命浪漫主义笔法写就的《柿子树》;我爱梁斌先生以现实主义手法写就的力作《水镜庄白马洞》;还有《寒江落日》中清俊与冷逸;《神圣的狼牙山》中的壮怀激烈;《真武山下》的真力弥漫;《风雨过山林》中的水墨晕章。
梁斌先生1993年创作的《纪念五一反扫荡51周年》,更是以浓重的笔墨、强烈的色彩和拙意的手法,与众不同地绘就了一幅浓烈的风景画,崎岖的田埂、饱满的莲子、满塘的荷叶、茂密的芦荡、弯垂的树木,所有的景物都统一在虽则稚拙但却如信手拈来的造型及笔墨语汇中。他的山水画还显现出画家深厚的生活底蕴。抑或是画家曾经战斗过并深情怀念的地方,抑或是画家采风或生活过的地方,在这些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浓厚的生活气息,提示了生活的本质和真谛,增添了画面的感染力。是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艺术创造。
文学与绘画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他们在表现人与自然的过程中也有相通之处。作为文学家的梁斌涉足绘画,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诗论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梁斌先生的画朴实无华、活泼率真、常带有一种稚拙,却绝无故作姿态或无病呻吟之笔。这是老子所谓“损之又损”而复归于“朴”,复归于“本真”之境界。
真正的艺术,总能够长久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它不仅是外在形式的表现,更是蕴涵于“形式”之内的一种精神张扬。梁斌先生的革命人文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红旗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中,也同样彰显在他的中国画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