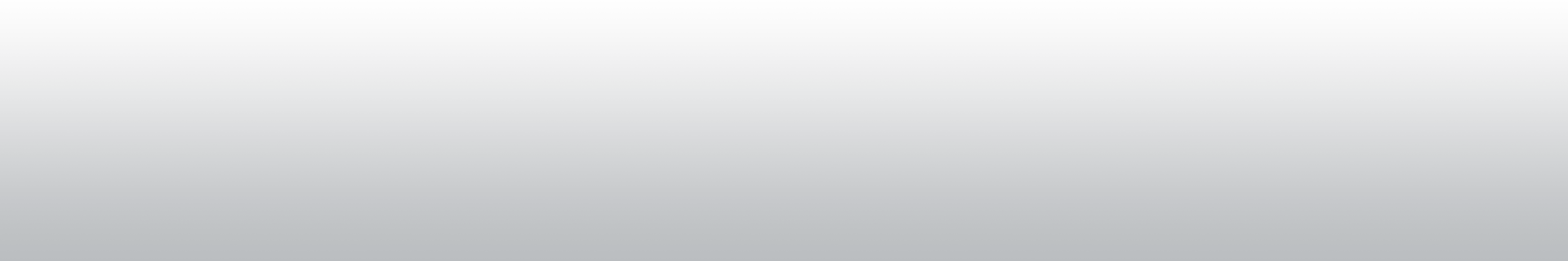一、花鸟画的写意传统
中国花鸟画的写意性,来自中国传统之文化观念的影响,是中国古典哲学与古典美学衍化与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思想中孔子的“三月不知肉味”切磋琢磨的执着;老子“善行无迹”的自然;庄子的“解衣般礴”的气势;以及佛家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超脱,给予绘画艺术以思想的深度,其思想内涵与审美取向构成了传统绘画的基础。就花鸟画而论,花鸟画家并不满足于对客观花鸟形象的摹拟,而是以自然中的景物生灵为参照,借助笔墨“托物言情” ,“托物言志”,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自然物象深刻体察之上的一种高度凝炼的情感表达。因此,中国花鸟画的写意性使人、社会、自然三者在绘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就审美本体而论,这种物我兼容、主客体统一的创作方式,则直接来源于写意性得以生发的主要思维方法——意象思维。
《庄子·天道》里说:“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认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意之所在,不可单纯以语言来完全说明;《易传·系辞》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是指这种体会。如何能解决表现的这种矛盾而做到主客观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艺术创作的难题,而首先要做到的是能够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所以庄子在《庄子·外物篇》中进一步阐释:“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易传》也有“立象尽意”之说,虽然这里的“象”主要是“卦象”,但为后来中国画艺术创作中的意象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导。在艺术创作中应达到“意”与“象”的统一,“意”为表达的目的,王弼的《周易略例·明象》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意、象、言的主次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明确的阐释,而正是这个“得意而忘象”使中国画的创作与审美从一开始就有了写意的观念,艺术创作者必须认识到创作目的在于“得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为文若此,绘画亦相通。
意象思维,是人的主观意志与自然形态的内在统一。作为审美意识,是美感形成的根源,是自然在人的主观意识作用下的人化。意象,构成了人与物象的交融,“吾心自有造化,静而求之”。[1]使画家在感知世界的同时,又在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反视自身,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升华,达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而作为表现对象的物象,经过作者情感与艺术禀赋的提炼,则形成了体现了主体审美思想的写意性绘画形象。因而中国花鸟画写意性的意象并不是执着于物象的自然属性,“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卉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画鉴》)
“托物言志”是指借助绘画作品中的具体艺术形象,以寄托物象之外的意旨。花鸟画即以花鸟形象为媒介寄托画家关乎人生的理想与愿望。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有的方式,密切了花鸟画与人类心灵的关系,形成了花鸟画审美方式上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早在宋代的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徐黄异体”时就指出:“谚云:‘黄家富贵,徐家野逸’,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徐熙、黄筌藉花鸟寄托其不同志趣,与来自于他们不同的生活环境所影响下的不同之人格体验,得之于心而应之手,从而形成的风格形态表现为“野逸”与“富贵”,达到了形式与内容、作者主观感受与作品风格的统一。同时也体现了自然花鸟物象由于审美主体思想的差异而带来不同的意象。画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花鸟画的论著《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云及:“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理焉。”道出了花鸟画的托物言志与文学传统有关,丰富了花鸟画的意象感受。这种传统由来以久,中国的《诗经》,已经反映了先民与自然生灵之间的审美关系。诗人以“六义”中的“赋、比、兴”为手段,通过对花鸟禽畜等自然美的描写,比拟人事,表现人们的内心感情世界。“比”与“兴”的艺术手段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中,本来就存在着比兴的心理因素。文学艺术则把这种精神加以强化,《论语》中借松柏表达坚贞的人格;屈原的《离骚》以美人香草寄托诗人的高尚情操;而这种传统表现在花鸟画创作上,则是画家结合自然物象的艺术特点予以表现,花鸟画中的“梅栏竹菊”被寓为“四君子”,松竹梅被寓为“岁寒三友”,牡丹寓为富贵,鸳鸯寓做夫妻等,正是这种“寓兴”在写意花鸟画中的体现。好的写意花鸟画作品自然能引发观者的联想与想象,唤起人生的某种情思与审美体验,从而也造就了花鸟画的审美趣味乃至品评标准。
二、超越时空的写意观念
在中国写意花鸟画表现中,并不拘泥于物象的时空表现特征,而是有画家主观情感上的超越。中国古典哲学认为, 气之聚散转化构成天地世界万物。天地间充满着无尽之矛盾,有与无、阴与阳、虚与实等等,而天地运动之和谐的原因是气,《老子·四十二章》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说文》云:“冲,涌摇也。”《淮南子·本经训》说:“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 其义充满生生不息,无穷变化之天地运动之壮观。“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为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具体到绘画作品的创作,就是写意画家对虚与实的认识,尤其对纸之虚白的无限生命意象的认识,简言之,纸的空白(虚无)使得笔墨及形象构成生命实现的运动特性。有与无的往复变化构成生命的无限发展,因此虚无的存在就不是空间的无物,虚无中有“气”之流行,“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3]佛家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是讲述虚无不空的思想。在绘画作品中,虚在有的对比下充满了极具意象的生命形象(“以有观其无”)而纸之虚白就是孕育艺术之象的母体,也就是混混沌沌大空间的存在。纸之虚白为画家抒发性灵提供了可能,是其自由表现的前提。所谓“计白当黑”之意就是中国写意画对“虚”的重要性具体认识和应用。
画史上,许多写意画家认识到这一点,八大山人一花一叶一石之�然不滓的简练笔墨,笔墨与纸的虚白浑然一体,让人体会出虚即实,实即虚的禅境;在他的众多以鱼为题材的作品,纸之虚白成为浩淼的水的意象与鱼的生命形象融为一体;所以,作为画面空白的水是虚,亦是实。与其他艺术所不同的是,中国写意画并不因物象的存在时空而制约画家的性灵,或纯粹走向黑白的装饰构成,而是最大限度的展现主体内在精神与自然之理的统一,由此而产生虽不符合“常形”,却合“常理”的中国写意画表现观念,所以,对纸之虚白意象的体认带给写意画家极大的表现自由,因而画家对物象的选择也就具有了情感上的主观任意性,由于对客观自然时空的艺术超越,因此在具体表现上,中国写意画的笔墨形式做到可以使画家性情与笔墨形式相契合而生发,所以写意花鸟画的创作过程往往是先有“胸有成竹”,然后一挥而就,但这不并同于先打粉本而后制作的有计划的创作程序,“成竹”是在内心。
中国古代有“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大时空观,花鸟画尤其是院体花鸟画在形似之中还要有时空的特定性,《画继》记载赵佶论画的故事,一少年进画月季花一幅,得到赵佶“赐绯,褒锡甚宠”,赵佶认为“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这反映了院体花鸟画在时空上的写实性。宋代文人画的代表人物苏轼也曾称赞赵昌的画“妙绝谁似昌”,称赞画中的黄葵“晨妆与午醉,真态合阴阳。君看此花枝,中有风露香。”[4]赵昌在画史上有“写生赵昌”之誉,其花鸟画之生动精微到特定时空下的生态。
对时空的敏感与表达似乎是中国人的天性,杜甫《春日江村》云:“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的辽阔;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悠长。这都是中国古代文人对时空意象的敏感表达。其实早在战国·楚《人物驭龙》帛画就描写了一个自由的时空:人、龙、鱼、鹤自由地在天地间飞翔;西汉·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描绘出了天界、人世间,海底到陆地的广阔的空间,而又有日、月置于同一时空。写意花鸟画在这种时空观念上的解放,如唐代王维画《袁安卧雪图》,雪中画上芭蕉,这显然是没有被客观时空所局限,强调主观精神之表现的文人倾向,沈括高度评价这种创造:“造理入神,迥得天机”。[5]在中国写意花鸟画的题材中,如《百花图》《墨花图卷》等题材把许多在生长季节、地域迥然不同的花卉集中于一纸,充分表达了作者的主观感受。天地之辽阔的“虚”,让万物众生流行不已,纸之虚、画家之“虚怀”也如“太虚”,可以容纳万物生灵之生态,可以表现自然之生命力,所以,写意花鸟画与其说对时空有所超越,不如说是对时空概念更全面的表达,是对自然生命更本质的描述。通过画家的最朴素的笔墨,描绘出花之清,物象之灵,人性之朴,所以,自然的精神不单纯局限于特定季节时令的形象,而是显示在其生生不息的生命流程中。这就要求写意花鸟的绘画语言在最大限度上的纯化,而又包含无尽的意蕴。一根单线的圆即可以是月又可以是日,时间在这种意向之中被延续;梅花、菊花同时被展现到一幅百花图中,季节的时差在这里被忽略,而四季的生命力由此得到集中表现,人的精神意向便可冲破时空的制约被集中强化为一体而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现。中国写意花鸟画达到的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如诗的境界,无限的时空变化与生命力的表现显示出质朴无华的境界。正因为中国画的写意性,花鸟画也凝固了一瞬间画家主体的心灵感受,这是好的艺术品之所以激动人心的原因,理性判断与诗意判断的分野即在于斯。
三、“迁想妙得”与写生、临摹、意创
我国东晋时,便有顾恺之的“迁想妙得”说,画史记载顾恺之画裴楷,颊上加了三根毛,人问其故,他回答说:“裴楷俊朗而有识具,此正是其识具。”旁观者认真端详,觉得特别符合裴楷的气度。[6]联想可以使创作者心灵自由敞开,启发艺术创作的灵感。其中主要强调的便是在创作中对所要描绘的客观物象倾注真挚的情感,通过联想去捕捉把握客观物象中抽象出来的精神,通过迁想妙得达到“传神”的境界。南朝的姚最在评价谢赫的绘画时说:“写貌人物,不俟对照,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精研,意在切似。”[7]这可以说是中国绘画中较早的写生记载了。北朝时颜之推也曾记载:“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座中宾客随意点染即成数人,以向童儒皆知姓名。”在中国画史上,一向不划分写真、写生或者是写意创作的具体界限。当画家在被描写的物象所感动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力量,便是创作者的最初直觉。
元之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说到:“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登楼望空阔处气韵,看云彩,即是山头景物。” 天空中云彩的动感,使人有意无意间发现新的形象,这正是迁想妙得的契机。
中国画对写生的理解,与西方绘画写生有着不同的内涵,除了有“摹仿”这一层含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体现自然之生意,得其虚灵。明之祝允明云:“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生者,生生不穷;“生”是指万物生长的自然状态,“意”是人们的主观感觉与自然物理相融合的产物,是人们对客观物象精神的摄取,是自然之生意。唐天宝年间,唐玄宗思念四川嘉陵江山水,因命画家李思训和吴道子去蜀地收集素材。其后,玄宗问吴道子的画在何处?他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于是唐玄宗命李思训与吴道子同画于大同殿上,李思训经数月成画,而吴道子凭借记忆,迁想妙得,一日画毕嘉陵江三百里山水。[8]从美术史上李、吴作品的风格来看,李思训的山水得其形似,而吴道子的山水则描绘的是山水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是通过迁想妙得来实现的,正是因为中国的写意绘画具备了如上的特征,所以中国的写意花鸟画并没有仅仅向如实的描绘物象之形似的方向发展,因而也就有了苏轼、文同之竹以及米元章的“米氏云山”。唐之张�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更体现了物象与画家们内心相契合的创作历程,“中得心源”是画家将“外师造化”所得的素材,通过集中、概括后在心中所产生的意象。“中得心源”的过程,实际上是把客观世界的“物”与主观精神的“我”统一的过程,也是表现画家鲜明的个性的过程。“若流电激空,惊飙戾天,毫飞墨喷。”(符载《观张员外画松石序》)从时人对张�作画状态的描述来看,这确是通过主客观和谐而达到的自由的创作境界。又如唐·韩�《五牛图》,画中的牛,各具情态,特别是画幅中间一牛的正面描绘,没有对牛的长期观察、写生与默记是很难做到的。韩干以画马著称,重写生,他曾回答唐玄宗说:“陛下内厩之马皆臣师也”。五代黄筌重视写生,常自养鹰禽,以观其生态,有明一代,大多的写意花鸟画家多画写生花卉,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陈白阳纸本水墨画《墨花图册》水墨淋漓、生意俱足,首页为文彭隶题“写生”二字,此“写生”即物之生意。还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沈周《花果》(长卷),他在卷尾自跋曰:“老子心无事,随芳学化工,满园红与白,多在墨痕中。”这一类写生题材在写意花鸟画中较为常见;清之恽寿平在花鸟写生方面达到的成就是同时代其他画家所难以企及的,时人评论恽寿平的画“一洗时习,独开生面,为写生正派”。[9]
从现存的宋人花鸟画来看,诸多的写生,大都应该是对物而作的,不然恐难以达到如此精微,只是它们在创作中又强调了“意”,肖似物形固然有之,而撷取自然生意才是最主要的,有观察之所得,也有感悟之所得。明之陈白阳尝云:“辛丑秋日偶从湖上来,逼留胥江之上,故人出名花、美酒,相赏忘归,解舟时,则花已在舟上,足知故人知我清癖,既至田舍,秉烛对花,篱落顿增奇事,不敢忘惠,戏写此纸复之,所谓名花即茉莉也……”“秉烛对花”这便是白阳山人的所谓的写生。晚于陈淳三十八年出生的徐渭,曾在其所画牡丹上题云:“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多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若风马牛,弗相似也。”所谓“多不见此花真面目”是画家强调了绘画中的主观因素,借花之形色去表现己之性情,去掉过多的理性及形与色的束缚,游戏于水墨之间。
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学习,一般由临摹入门,以便于掌握最基本的笔墨技法、造型及构图程式。入手较高,多看多临,目识心记,久之能使法为己用。对于已经掌握一定的笔墨技巧的学画者来说,有目的地选择临摹经典作品,有利于提高笔墨纯度和对于前人(古人、今人)艺术风格的借鉴。但对于已经具备创作能力的写意画家来说,临摹仅是对前人作品气骨风神的追思、借鉴,或取其构图,或取其笔墨趣味,或在前人作品中提取与自己之艺术风格的同构因素,深入诣趣、阐发幽微。这种临摹与初学者相比较有着本质之不同,借鉴的目的是为了意创,可以说这种临摹已经包含了相当多的自我创意。董其昌学米氏云山,八大学董其昌,弘仁学倪云林,四王学元人,历代文人画家所谓仿某家,法某家的过程,其主旨便是借古以开今的意创。他们往往借经典作品风格之大意,或与古人意合神侔。而在他们题为仿某家的作品中,往往通过意创呈现自家面目;故能随意拈来,皆有我在。如陈白阳对米家山水的意创,便是他在一己之体验中,归纳二米、高克恭之画风,充分利用自己之用水优势,则“烟林云壑,墨气浓淡,一笔出之,妙有天机”。[10]所谓“一笔出之,妙有天机”是说他在法古的同时,一气呵成,水墨冲淡,灵动无方而又妙合自然之理,画风得之二米而又有出于二米之外的意趣。 “春山�郁,烟云变幻触目成画”,[11]“试问如何闲得甚,一身清癖米家风”(陈淳《白阳集》)。在陈白阳的写意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画,其所云的仿某家、法某家画法皆仿佛而已,这便是陈白阳的意创。其作品的内在风格主要来自他放逸出尘的性格与如野鹤闲云般的高士情怀,而对自然的亲近,对大朴无华的心灵体验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写意画家共同的特点。
[1] 清·戴熙《习苦斋画絮》。
[2] 《庄子·人间世》。
[3] 宋·张载:《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卷一,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9月版,14页。
[4] 宋·苏轼:《净因院画记》。
[5] 宋·沈括:《梦溪笔谈》,选自郭因:《中国绘画美学史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8月版,140页。
[6]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晋》卷五。
[7] 姚最:《续画品录》,选自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3月版,20页。
[8] 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9] 林树中、周积寅编《中国历代绘画图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12月版,162图。
[10] 清·方薰《山静居论画》。
[11] 明·陈淳《仿米云山图卷》(纸本,墨笔,美国王己千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