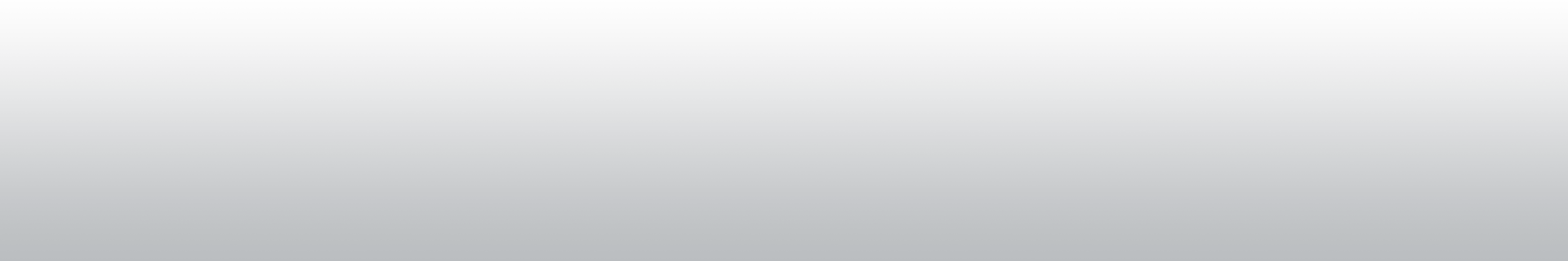一、从复杂走向单纯
禅是梵文Dhyana(禅那)音译的略称,意译为“思维修”、“弃恶”、“静虑”、 “功德丛林”等。按修习之次序又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种,称“四禅”或“四静虑”。中国的禅宗便以“禅”为宗派之名称,宣称“妄念不生为禅,坐见本性为定”。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离念。”(《坛经》)神会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说:“六代大师,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梯。”再借用一位日本的现代禅学大师铃木大拙通俗的话来说,“禅宗的特色是:喜纯,诚挚,与自由。许多想研究禅宗的人,对自由有很大的误解。他们以为自由是纵情放任或不顾道德。但是真的自由,我愿说,是照着事物本来的样子去看它们,是去体会万有的‘本来面目’。那才是自由”[1]。人的本心都是清净而圆满的,心外本无佛,只是由于“颠倒梦想”构成了“烦恼障”,物外挂碍构成了“所知障”,佛家认为众生只要能内证本心,皆可成佛,获得解脱的真正自由。《坛经》云:“去来自由,心体无滞。”“ 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般若品》)“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行由品》)铃木大拙在《禅与生活》中说:“从本质上看,禅是见性的方法,并指出我们挣脱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由于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泉源,使我们摆脱一切束缚,而这些束缚是使我们有限生命时常在这个世界受苦的。”
黄檗断际禅师认为:“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2] “禅的终极目的,乃是破除人类的妄情偏执,妄情偏执本非圆融无垢的自心所固有,只是因为你的颠倒梦想,使你烦恼丛生;而偏执之知,更使你背离万法的实相。只有将这种有障有执的根本错误去尽,那时你才证得了自心的无上菩提,把心量放大到无量无边,与宇宙真正契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刹那、一微尘与那无始无终、无边无中的宇宙同在”[3] 在禅宗学说中,认识真理的道路不是从众多走向众多,从超验走向超验,而是从众多走向“一”、走向个体,从复杂走向单纯,从有形走向无形。“一”与“无形”的体现是直接的,自由的,无挂无碍的。这个“一” 之表现和存在于众多之中,无形则表现和存在于众形之中。所以,禅宗写意画家不为表达众多而体现众多,不为体现众形而描绘众形,对于他来说,众多是用来表现“一”,反之“一”是用来表现众多,而形是用来表现无形的精神。
禅宗学说在绘画上的启示便是中国禅宗写意画超越于形象色相,在创作上不执于一笔一墨之形似,以单纯的笔墨来描述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内心最直接纯粹的真实状态,同时又不流于抽象之空洞的极端,流于抽象的形式和拘泥形似的呆板如同执于“相”和执于“空”一样,不是真解脱真自由。艺术家画的是“意”,禅宗写意画是对平凡事物的超越“相”的认识,不是对平凡事物的简单否定,也许画面上只是一株草或一块石,但那是作者之禅意,是作者的心境体现在所画事物的“本来面目”。与老庄之“道无所不在”的体验相契,唐代顾况《画山水歌》说过于此类似之意:“山峥嵘,水泓澄,漫漫汗汗一笔耕,一草一木栖神明”。宇宙万有生灵与画者为一,灵气相通。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承续了这个观点:“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岂独山水,虽一草一木莫不有性情,……画与写者,正在此着精神”。如果画者真正达到如此“齐一”之境地,彼之性情即是此之性情,观画者也是能体会出作者之心境的,《广川画跋》(书李成画后)中说:“观咸熙画者,执于形相,忽若忘之,世人方且惊疑以为神矣……彼其胸中自无一丘一壑。”
水墨写意画对形、对色彩描画之法的超越与解放,这也是写意画把世界纷繁之变化单纯化的表现,老子说过“五色使吾盲”。《金刚经》也有偈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些“音”“色”之相是求证佛法的障碍,是见“自性”的障碍。执于色彩,必定执于每一笔色彩的变化与和谐,便是抒发“意气”的障碍,唐代张彦远说:“夫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忘言,神工独运,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粹,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4]这里张彦远认为自然之色彩为自然而生,绘画的价值并不在于这些“五色”和“巧密”,而是要“得意”,“自然为上品”。元之倪瓒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又说:“余之竹,聊写胸中之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5]《画鉴》:“花卉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陈去非诗:‘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其斯之谓欤!”即是对世界的单纯化把握与理解,认识到诸相之虚妄,而回到万物之齐一与心境之本源。
二、超越与自由
禅宗六祖慧能认为,真谛实相不在外境,而在于本来纯净的内心,“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坛经》)人的原初的心性是真实无碍、澄明干净的,只是由于世俗的思想、欲念和业力的作用在心性上染了“尘埃”,“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便显现不出清净自然之本性。《金刚经》中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诸相”都不是实有的,所谓《金刚经》偈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人心本来无一物,是澄明的,应破除对 “相” 之执著,当我们能看到“诸相”的“虚妄”,超越于世俗所谓的“有”,认识到事物“成、住、坏、空”的发展过程和“无常”,以至体悟到事物和内心的“本来面目”,便能见“如来”。这种超越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不是从有走到虚无的空,不是从一端走到另一端,而是“真空妙有”,所谓“心经”即:“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既是空,空既是色”。《坛经·机缘品》云:“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这真是一种心灵上完全的对逻辑理性的超越,这不是简单的否定与肯定的关系,也不是肯定之中有否定,否定之中有肯定的辩证关系,而是本来如此,何有分别与不分别呢?所谓“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净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当禅者“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认识到“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时,便能“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
佛教禅宗的对人性的彻底解脱和自由在艺术里转化为作者对艺术创作的一种解脱与自由,以及艺术家对艺术纯粹性的理解,这种纯粹包括艺术语言与思想的纯粹。“你是否已经与你自己进行纯洁的交往,无沾无滞地与你自己契合为一体,没杂质和你混在一起?你是否已成为一种其大无穷,其形难状,不增不减的光辉?如果你已达到这种境界,你就已变成一种所见境。”。[6]禅宗写意画摈弃了书本技法教条的羁绊,对于如何描述出禅的境界,也从以前的对于神圣的、超验的佛、乐土乃至于整个神话之信仰和偶像崇拜中解脱出来。艺术家自由的去体会自己周围之事物,或为眼前的一株小花;或为自由流淌在山间小路边的小溪,或为自己一瞬间想到的先贤高德之像……这不可尽述的意象不必精描细画,只要作品的艺术形象是无形之“我”的表现,那时“我”即是佛,是“我”的本来的心。这个“我”所表现出的世界当然是真实无碍的.即便禅宗写意画家运用传统的佛教题材,他们也不是用超验的、神秘之眼光来看待它们,而是以人类之观点来看待。与其他学说不同,禅宗学说不具有分析推理的性质。其他学说确立了达到最高境界的各种层次之方法,而禅宗写意则认为一笔下去即可抓住事物之 “神”,一画就可将它体现出来。明末清初著名画僧担当禅师曾说:“若要图真便失真,谁知格外有高人,好将刻画都焚尽,潦草堪传顾陆神”[7],画者并非是为了“图真”,如果只是为了表面形体的真实,便要“失真”了,要去体悟到事物万有之“本来面目”,那便应是自由的,真实的,信笔“潦草”那也是能体现出传神之境界的。石涛云“一有不明则万物障,一无不明则万物齐。画之理,笔之法,不过天地之质与饰也。”“我有是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8]也是讲作者应体悟“真如”。
佛教禅宗在唐与南宋达到鼎盛,此时之绘画也得以更自由的表述,人们认识到形的过分描绘对于写意之局限,因而对绘画的理解也便进一步纯粹。明末董其昌将绘画的“南北二宗”以唐代为界限,“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9]苏轼,董其昌等把文人画之鼻祖指向王维,这亦并非偶然,苏轼在《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诗说:“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似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10]在这里王维之所以被评价的特别的高,最大的原因在于王维信奉佛教以佛弟子自许,以禅理入诗,又以诗意入画,创“破墨山水”。对于其后之水墨画的发展影响很大。
唐代符载的《观张员外画松石序》记述张�作画状态时说道:“若流电激空,惊飙戾天,催挫斡掣,�霍瞥列,毫飞墨喷摔掌如裂,离合惝恍,忽生怪状。及其终也,则松鳞皴,石�岩,水湛湛,云窈眇。投笔而起,为之四顾,若雷雨之澄霁,见万物之情性。”他在其后分析道:“当其有事,已知夫遗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徒。若忖短长于隘度,算妍蚩于陋目,凝觚舐墨,依违良久,乃绘物之赘疣也,宁置于齿牙间哉?”张彦远在说得更是直接:“是知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11]只有心灵上的完全自由,认识到万物和自身的“本来面目”,才能达到无所畏惧的大自由之境界。荆浩在《笔法记》中评价:“张�员外树石,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旷古绝今,未之有也。”禅宗写意画的自由是佛教禅宗之大自由意义在绘画创作上的体现,一切以心的自由为源,是张�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范宽说:“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也。”[12]即如禅宗意。由此在写意画中认识到了绘画的精神——在绘画通过“心”来达到对物我精神的交融的体现和超越,从而体现出绘画创作之自由与解放。“即以墨泼,或笑,或吟,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13]在这种“解衣般礴”式的超越中,追求到自然而然的境界,张彦远说:“夫运思挥毫,意不在于画,故得于画矣。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不知然而然。”“自然者为上品之上。”[14]六祖慧能形容修禅的自由状态“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坛经?顿见品》)。石涛形容艺术创作之自由:“此道见地透脱,只须放笔直扫,千岩万壑,纵目一览望之,若惊电奔云,屯屯自起。”(石涛《画语录》) “见地透脱”是心灵的自由,是体会万有之“本来面目”的自由,是艺术思想的自由与纯粹。“放笔直扫”是对艺术语言运用和对作画材料掌握的自由,是超脱于形和技法之自由。“千岩万壑,纵目一览望之,若惊电奔云,屯屯自起”是作品达到的那种与自然不二之效果。艺术的精神是在心灵自由纯粹以后达到绘画的大自由的境界,超越于形的束缚,超越于技法之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