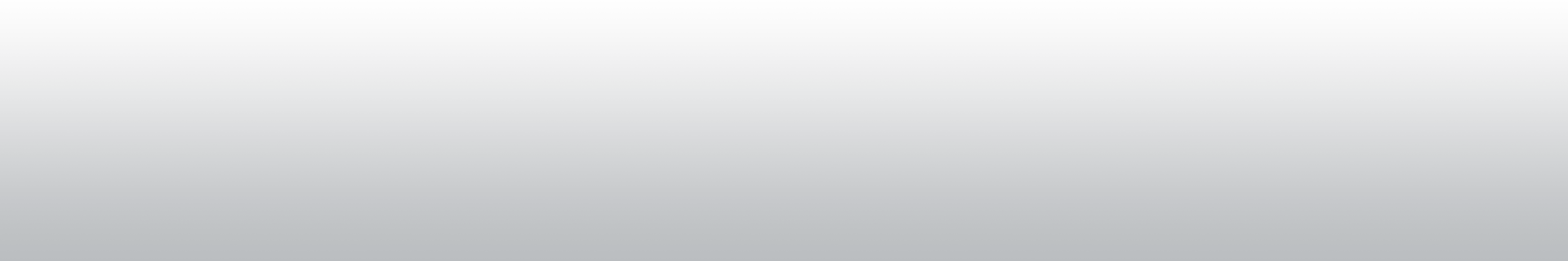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戊寅某夜记事
那天晚上刚刚下完雨,一个人沿着河边慢悠悠地走,风儿清凉,天很黑,前方楼上的灯光映得湖水亮亮的,近处的花丛已过了开花的季节,茂密的叶子映和着灯光,有着许多闪亮的光斑。前方小树林里的杨树尚未成材,一株株直直地上指,连成一排,网成一片,给人以快意的感觉。
这河底的水边原本有一条小道,闲暇的时候,你总爱于晚间在那儿独自徜徉。因为近日里暴雨连降,现在睇目视之,那条小路也被新涨的河水淹没了。若是在故乡,在这样的水边,早已能听到许多蛙的连唱了,而这儿的蛙鸣似乎稀疏得多。
你正值“青春作赋”的年龄,心应无碍于物,嵇中散云:“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噫!此岂不令人心仪神移耶。而此时,你所记起的却偏偏是阮中郎的《夜中不能寐》诗中的句子:
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是以又想起故乡,郁郁累累,也仅是“远望可以当归”了。白天,好友劲松寄诗集来,其中有一首题为《乡土》中的几句,对你颇有些触及:
有一年下雪
想起故乡
我的布衣口袋里
盛满泥土的真态
它的崇高和灵透
……
在逝去的冬天之下
……
很久以来,对于故乡,你的情感始终是炽热而又复杂的,有着隐约疼痛的美感,总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但每次拿起笔,又不得不放下,有些沉重。
风起了。
回吧。
(1994年3月)
●等 待
在日落之前,因为一件本不应有的事情耽搁了时间,在幼儿园里,三岁半的儿子正依着年轻的柳老师,痴痴地张望,等你出现。虽然,今天是儿子入幼儿园以来你唯一的一次迟到,但你却不能原谅自己,或许是你少年的时候,有过太多的等待。
少年之与你,似乎有着太多的断续与等候。于是你习惯于把自己沉浸在画里,你画原野上的绿树、溪边的青草、成熟的麦浪;你画无声的小河、寂静的村庄、隆冬里的雪野和在春天里开满黄花的小园。那里有你的梦想与希望,有你能够贯彻始终的愉悦。
那一年秋季的傍晚,望着远处村庄方向缕缕升起的炊烟,渐而是头顶上慢慢明朗的星星,你在野地里护卫着生产队分给的红薯。不远处有磷火,风吹着谁家坟头上的老树叶子刷刷地响,有些冷也有些怕。你在自己小小的心眼里估摸着时间,盼望渐而渐近的挂在板车上的马灯的亮光。一次又一次地,时间过得真慢,直到很多年后你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郁郁而悠长的曲子。那一年,你初中一年级,因为一时觉得有趣,便给邻村的一位民办教师画了一张像,没想到这位有着些暴戾秉性的先生便认定这是对他人格的“大不敬”,以至于你最终不得不离开了那所学校,而不久,那所原本凑合的中学也便解散了。而因为崇尚先祖的德行以至于把天下读书人都看得神圣的爹却仍然决定让你体验一段劳动的感觉,于是那段时间里你竟成了当时村里劳动力中最小的一员,也是从那时起,你便学会了锄地、割麦、插稻等多种活计,于是也便学会了忍耐或者说等待。夹在密密的作物间,你面对的不仅仅是怡然的欣赏——小麦遍地的金黄、红薯成熟后的棵棵隆起、玉米穗的颗颗饱满,而更多的是面对着一种劳作,一种从一开始就对收工的期盼。好在这段时间维持得不长,半年后区里新组织的“联中”成立后,当父亲要你在继续劳动或者是上学两条路中做出抉择时,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学。
你那时在相隔二里地的“联中”读书,每天晨起的时候,天都不会亮,黎明前你常常一个人背着书包走在土路上,害怕的时候,就大声地唱一首歌,或胡乱地喊着些什么。
就在你读“联中”第二年的“六•一”,县城里举办中小学生书画大赛,到了暑假前的某一天傍晚,学校里通知说你的书画作品在县里获了一等奖。你记得当时的心情很激动,斜阳格外柔和,红霞烧遍了西边的大半天空,于是,你兴冲冲地回家告诉母亲,娘却说,她早就知道你会得奖的。
三岁半的儿子性格很像童年时的你,他天真、活泼,而有着天性善良的冲动。那日,儿子在夕阳的余晖里奔跑、爬滑梯、穿山洞、坐船、跑圈、开火车、坐飞机,凡幼儿园里有的,你都让儿子玩个够,然后你们去麦当劳、肯德基,直至儿子说:“爸爸,咱们回家吧!”你这才意犹未尽地把儿子抱上了摩托。
(1998年8月)
●静静的村北
在春天,阳光灿烂的日子,你看见那个少年斜倚在村北的一棵老柳树旁,身边放着一条细细的竹竿。半晌午的时候,大人们大都在田里劳作,村北的菜园里静静的,而这也正合少年那安恬好静的心性。乡村里出没的鸟类很多,只是庄稼人总是在匆忙中,难以注意到僻静处除雀儿以外的鸟儿们,但在这时,树丛中、树梢上或晴空里,往往会飞翔着如画眉、白头及一些不知名的好看的鸟儿,不同的鸟鸣在村北这块幽谧的氛围里汇成一支婉转而有韵致的曲子,而各色各样的鸟儿或低飞,或高翔,或疾或缓,或随风浮动于树梢,或呼应嬉戏于林间田头,又把这块本来略显单调的空间装点成一幅极富动感的画面。
在这一年长长的春天里,家里人依然总是要嘱咐少年别忘了读书,父亲虽则严厉,但毕竟疼爱自己的儿子,自从经历了那次给老师画像事件后不久,虽然也让他大大地经历了一通劳动的“洗礼”,然后便悄悄地更换了少年在劳动中的位置,在那一年的春天里,他唯一的任务似乎便是每天去村北的菜园看菜。每天,在少年的书包里,除了必备的课本外,还有他在几个哥哥不注意时,悄悄装上的一两本小说,大体不外乎家里仅有的几本《元代戏曲选集》,以及《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这其中的两本,在小学五年级时,他已读过数遍,虽则有许多的字并不认识,但每一句的大体意思都是知道的。以至于他有时出现了失眠的现象,脑海中每每多了些奇怪的念头,做梦时也常常梦见妖怪一类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忽而变成了古时跨马提枪的英雄。故事情节自然是来自小说里,而形象的设计当然便是从同学手中借的小人书上的画面了。以至于后来少年便开始了逃学生涯,学校上自习课时,他便拿起自制的鱼筐到水塘边捉鱼。每次,随着鱼筐渐露水面,看得见里面翻转着一条或数条青青而略透明的背儿和银白色的胸腹时,少年都会感到异常的刺激与惊喜。而这一年的春天,再没学可上了,少年便在这村北的菜园里读完了两本《元代戏曲选集》。在这期间,他必须每天在几个哥哥回家前,将这些书收好放回箱底的原处,丝毫都不敢大意。在这年春天,少年临摹了这两本书中所有的明代木版画插图和《三国演义》中的部分插图,并用仅有的一盒水彩色根据自己的意图给它们染上颜色,再把它们张贴在自己小屋里的土墙上,常常自以为得意。
在当时,父母只是一门心思让少年能好好读学校的课本,并企图让少年将来光复祖上曾有过的荣光。只是少年并不争气,只爱读这些半懂不懂的“闲书”,但无论如何,当父母一见到自己的儿子在读书本而不是在捕鱼、听戏、听大鼓或晚上去几里外的乡场上看露天电影或别的,那种欣慰与希冀交织着的复杂情感便会溢于言表,这使得少年幼小的心灵里也会时时生出些愧疚。
那年的春夏之初,当时远在内蒙古工作的三哥给少年寄来一套有关绘画的资料来,有《西洋绘画技法》、《实用人体结构》,这对少年无疑是如获至宝,于是日日临摹、日日默写,常是把一本资料完完整整地临摹数遍,直至连同上面的文字都能一一背下。在这偏僻的乡间,这种朴素的学习方法也无疑为他日后的升学打下了基础,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他每有念及,常常为此而感到庆幸,而这一切,似乎又同三哥当时的鼓励不无关系。
而今又到了春天,在故乡的村北,是不是依然有着满园的葱绿?故乡的门前,那架用来遮挡风雨的棚子是否还立在那儿?表哥用余料做成的木制画架还在吗?
(1998年10月)
●雨 夜
午夜,你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见和儿子一路走来,像是走到了老家的某个地方。那儿有宽敞的院落。你梦见儿子倚着你站在老家的木门廊下,初夏的雨也就大了起来,打在门前葡萄园的藤架上,打在老柳树下的园屋上,打在花椒树的叶子上发出沙沙的响声,雨水从木叶上滴滴落下,晶晶莹莹的。雨点打在沙土上溅起泥土特有的腥味,让你感到亲切。雨幕在平原的上空留下道道印痕,葱葱郁郁的原野被披上一袭空■的轻纱。这一切,都令你感到新奇与冲动。
你梦见你的死亡,你如此清晰地选择了死,你的思想也便穿透了无边的黑暗,你的躯体也便轻轻地穿过你生前无法逾越的层层围墙。
你梦见你在空中向下俯瞰,你看到你的儿子流落在荒岛上,四面的海水无尽无涯,天空布满了乌云,鹅黄色的云头弥漫在儿子头顶。在暴风雨来临以前,鱼儿纷纷在浅水中游动。沙地上的蚂蚁乱纷纷地忙着搬家,远方有隐隐的雷鸣,你看见儿子就坐在礁石上,望着脚下清澈的水中,鱼儿在石隙间自由地游走,看着鸥鸟一群群地在海上飞翔,你禁不住俯下身来,怜爱地抚摩儿子双肩,然而儿子却一点也不觉得。你看到天那边的雨幕在迅疾地推进,你呼唤着儿子快到岸上的荒崖下躲避,儿子却听不到。“哦,我真的已经死了!”你恍然而悲怆。
雨停了,太阳从云层中射出一道道如梦如幻的光亮,云霞罗列,一排排直至天际,海边湛蓝,沙滩金黄,你看见儿子脱下自己被雨水淋湿的衣裳,把它放在礁石上,然后傍着沙滩,如你儿时那样地静静睡去,如你幼时那样做着甜甜的梦,你就这样长久地注视着儿子酣睡的姿态。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倏然,一匹黑骏马嘶鸣着疾驰而过,鸣叫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儿子,你看见他捷然跃起,骑上马背。而黑骏马亦如见到主人般的温顺。在碧波万顷的海上,如行云驾雾般地背负着儿子游向远方。“儿子!”你在梦中都喊出了声。
你从梦中倏然惊醒,才发现三岁半的儿子已然从你身边醒来,小家伙正摇着你的胳膊,向你要水喝。你可爱的儿子喝完水后便又重新睡入了梦乡,熟睡的姿态呈“七”字形,双腿都搭在你的胸脯上。
在这静夜里,窗外依然下着雨,在幢幢高楼的遮蔽下,看不见它的形迹,只是在夜车隆隆驶过时,才能感到骤雨的沙沙声,甚至感觉得到它冰凉的体温,全不如故乡的雨轻柔与感人。
(1998年11月)
●北沙河
黄河曾经从这儿流过
于是在千里的平畴中
就有了一片片河滩
如同一条金线缀起一串珍珠
曾几何时
这里的河流枯槁
只留下点点星光
像故乡大沙河中
方圆不大的清潭
潭水娇嫩而轻柔
为你准备了一生的梦想
那是一个极其宁静的乡间午后,村北三里之遥的大沙河里的水几乎全干了,只留下涨水时,河床决口处的一处积水潭。晌午后,在这儿张网捕鱼的几条汉子都已回家了,只剩下你自己坐在静静的水边,看那些惊惶了一上午的鱼儿纷纷浮出水面。尤以细长的白鲢居多,如木梳一般大小,还有些细小的鱼儿,呈半透明状,游得极快,你最爱看一些长有花斑的小鱼,往来于水边的沙石缝隙间。水儿清凉清凉的,你在水中玩耍得痴了,都忘了回家的时间。
午后的日光暖暖地照着,四下里没有一个人,岸上小杨树的叶子发着细微的沙沙声。村子似乎离你太远,你有时从水中直起身向远处眺望,看到的也只是一片片泛着金黄的麦浪和远远的村庄的影子。不知又过了多久,堤岸的那边传来吹吹打打的喇叭声,渐而渐近的,一队身着孝服、发着呜呜咽咽哭泣声的人群从堤岸上缓缓走过,翻飞的纸钱都飘落在不远处的麦梢上。你便光着小屁股从水里爬上岸,站在那儿远远地看。你知道那是邻村的一个女人,就在前天傍晚,邻村的几个中年汉子,站在断墙上,声嘶力竭地喊着:“回来吧,回来吧。”一边喊一边用木棒敲击着簸箕。你便问身边的大人:“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大人说:“在叫魂!”“什么是叫魂?”你又问。答:“上吊死后不久的人,她的魂儿还没去远,如果站在高处大声叫唤,她听到了叫声便会活转过来。”看来,这位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终于也没有听到人们的召唤,抑或是她听到了也终于不愿意再回转来呢!送葬的人群渐渐地远了,大沙河里又变得静静的,甚至有点让你发慌。但在那时,你不会把死亡与自己联系起来,更不会去想自己有一天也会死的,只是就在昨夜,你又梦见了自己的死,似乎没有那么的痛苦,只是你身在异乡,没有人站在高处替你“叫魂”,你觉得很孤单。
那年夏天的那个午后,北沙河里一片静寂,你于是便一手拿着自制的小网,一手提着已湿透了的布鞋走上了回家的那条小路。你看到一只牵牛在杨树身上慢慢地爬,黑黑的背上撒着些白色的斑点,就像现在作写意画时用毛笔在上边胡乱弹了些白粉,两条须子一节节地长长地翘在前边。你便将它捉住,再从麦田里折上一根麦秆,然后把它插在沙土地里,看着牵牛在上面爬上爬下。那牵牛爬得真慢。
那天午饭时,家里人发现你不见了,全家人都着实地慌了神。尤其负责看管你的三哥自然是难免被娘一通唠叨。当你泥巴巴地出现在大门口时,你看到全家人表情各异。那天下午,娘把你捉到的仅有的几条小鱼和一条泥鳅用荷叶包好再用泥封上放在锅底烧熟了给你吃,那香味也便常常地留在了你的记忆里。
(1998年2月)
●父 亲
父亲的一双手上长满了老茧,冬天里,指掌间一道道的裂纹纵横交错,龟裂得深的地方总有点点的血色隐现出来。五指平伸时就像枯树的树根般有着坚硬的苍赭色。指甲厚而硬,剪都剪不动。儿时的我有时在想,为什么我的指甲又薄又脆不像父亲。
父亲十八岁时便和母亲结了婚,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养育了八个孩子,又都让他们上了学。这在那个偏僻而又贫瘠的乡间着实不容易。好在父亲是村里出了名的“能人”。他能吃苦,手艺好,其实这里所说的“手艺”也不过是乡下人借以维持生计的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比如种菜,父亲会种各种蔬菜。每年春天,菜花便开满了菜园,这也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有些蔬菜会一直留到秋天,收下来时便可得到许多蔬菜的种子。通常在这个季节里,父亲总要出远门,有时一去十多天。等卖完菜种回来时,便会带一些好吃的或好玩的给我们。同时,哥哥姐姐们一年的学费、家里一年的生活费才算是有了着落。
我那时很小,父亲出门时,不会带我去。只记得有一次,父亲在外出时顺便把我送到亲戚家。不想在半道上天下起了雨,父亲便把衣服脱下给我披上,推着那辆旧自行车,淌水过了河。深秋的河水清清冷冷的,水边上长满了草绿色的苇子,有蛙在不停地叫,在雨中,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在村头找到了一间牛车屋。雨依旧不停地下着,正午时,疲惫的父亲在牛车里睡着了,而我只是觉得新鲜,扒着车帮,看雨幕下的天空、池塘、老柳树、草屋都被笼罩在雾蒙蒙的雨幕之中。有一段时间,雨偶尔停了下来,但不一会儿,又有大片的乌云涌来。在暴雨来临前的阵风里,几个出来玩耍的孩子一边跑一边唱:“风来了,雨来了,老和尚背个鼓来了……”我便记下,自己也在心里悄悄地唱。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天亦然在下着雨,我把这首歌谣教给了三岁半的儿子,不自觉地,两行泪便顺着我的眼角静静地流了下来。
在这座北方的城市里,十二月的天气,天还未全黑下来,雾气便已弥满了天空,而滴滴答答的雨声使得这一片灰色显得愈发沉重。
隔窗向外望去,三两株落了叶的榆树湿露露地从窗户的一旁斜斜地伸出老远。透过树丛,不远处学堂里的灯光在渐而渐重的雾幕里隐约可见,迷迷蒙蒙的。
三岁半的儿子趁我不注意时,爬上了窗台,我吃了一惊,急着要把儿子抱下来,可儿子却硬是用手拉着窗棱不肯下来。情急之下,我便在儿子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儿子转过身看着我说:“爸爸,我不要你了。”语气中似有着些许惹人怜爱的郑重。我于是又想起了父亲。父亲打过我,在我记忆中只有一次。那一年我从上中学所在的县城回家过年,年三十,按老家的风俗,父亲买了一大盘鞭炮,放炮时,通常是将一大串鞭炮拴在一支竹竿上或是挂在树上,用火点着鞭炮末端的捻子,便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可不知为什么,那天在我点着鞭炮后,那串炮便落在了地上,这按乡村里的规矩,便是不吉利的。我记得当时气急的父亲踹了我一脚,我很委屈。再后来,每年过节时,我都要亲自点放鞭炮,赌气般地。父亲便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并不说话。久之,每年过年由我亲自放鞭炮似已成了我们家的定则,而我也早已不再是为了赌气,而是为了预祝来年的顺利或者说是让老人有个好心情。其实父亲一向并不迷信,只是那几年家境艰难,庄稼欠收,蔬菜卖不上价钱,母亲又多病。这些,在父亲的心里无疑都是一种沉重的负荷。现在想来,我也愈发能够理解父亲在当时的心情了。
在家里,父亲总是很少说话,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好像从来没有清闲过,关于农民,人们在赞美其勤劳之余也每每不屑其愚昧。而我的父亲为了八个孩子,也使尽了所有的能力与气力。因为他再也不愿他的子孙继续他的生活。每每提起上学,父亲给我们提及的便是先祖的荣耀和老家那边纵横着的许多御赐的碑林。父亲也时常叹息,这是因为当年在山东做武术教师的爷爷没能让父亲读书的缘故,但父亲很少说出口,这是他的隐痛。
我在上中学时,从乡下考到了城里,那天,父亲骑着自行车一直送我到距村子十八里外的黄口汽车站,一路上,父亲都很少做声,只是在汽车就要开走时父亲才说:“六儿,你要争口气,好好上学,在家里不容易。”我默然。在行驶的汽车上,我看着父亲一直就站在那儿,直到汽车拐到了土坡的那边。
有一年,一个远门亲戚来我家提亲,因为在我们家乡,十七八岁的男孩通常便要娶亲生子另立家庭了。而这时也便是许多正值上学的学生终止学业的时候,父亲就说:“六儿正上学。”那家亲戚便反复地劝说父亲诸如附近村子多少年都没有人能考上学云云,热情而又中肯。父亲沉默了许久,说:“等开春,我把家里的牛卖了。只要食能供上,还有不下蛋的鸡吗?”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父亲的一生都在为他的八个儿女奔忙,却从来没听说过父亲自己需要过什么,从来没有。这些年,我们都相继长大成人并离开了那个村庄,偶尔回家来看看老人,也都是匆匆去来,而每一次,我都发现父亲似乎又苍老了许多。似乎有许多话,都说不出,我只是让老人坐好,然后斟上一杯酒给父亲。待再喝时,一旁的母亲便说:“不能再喝了。”父亲脸上也有了以往少见的笑色,说:“不喝了,不能喝了。”
(1998年5月)
●听箫少年
一个晴朗的霜晨,在这条用碎石铺成的小路上,在日光的灿环中,你看到一个衣着朴素的少年的身影,他来自小巷的那一边,斜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黄书包,腋下还有一只画速写用的夹子,匆匆地,从你身边走过,看都没有看你一眼,待你呼唤他时,却已没了踪影。
黄昏前,你凝视着那条深巷,如一株老树立在深秋的风里,你就这样一直地凝视着,再不见那少年的影子。
黄昏里,你来到西山的林间,天空上,月儿依然照着山坡下的溪水,你掬了一捧在手中,亮亮的,那个少年就站在几步以外的地方,梦幻般地。
黄昏里,你看见少年常常在暮色里漫步,迷蒙的月色亦如少年惆怅的心绪。在西山的一隅,在疏疏的松林之间,在竹篱茅舍的纱窗里,常传出一阵凄迷的箫声。这哀婉得近乎凄美的曲子,每每让少年流连忘返。渐渐地,那幽渺奇绝的箫声便浸透在了少年的生命里,再后来,在每个日升或日落的时刻,或者是在静静的午夜里,少年都常常会向着远方,想些什么……
前些日,你拿着一叠刚写好的稿子给一个当编辑的同乡看,老先生说:“其实你还很年轻,缘何每每这般细说从头?”老人家的好意,你自然是领会的,而乡愁淡淡,缠绕脑际又不得不写。你自问,你难道真的颓废了吗?!都辜负了辛勤哺育你的善良母亲。每一次想念,都会让自己猛然心冷。
热风吹来的烦躁深入到了心里,冷风吹来的黄沙淹没在眼里,黄昏笼盖了旷野,你独自伫立在秋夜,露水打湿了你胸前的衣裳。
又到深秋,黄叶游离在枝头间,月季花婆娑在秋风里,关于青春的传说,似乎已很遥远,又似乎还没到来。只是当你一个人独自静对、凝望,有时会看到那少年的影子。
(1998年6月)
●母亲 艺术 平常心
在儿时,艺术,我曾和你相遇,如那个双手举着火把,颤颤然进入阿尔它米亚山洞的孩子,面对着崖壁上睁大眼睛的野牛画像,好奇与崇高感同时占有了她的心灵,而那灵性也溶入了我的心里,雕塑着我的人生。
那孩子不知道远祖们在崖壁上绘这些野牛意味着什么,正如我儿时之与艺术。又如再过多少年,人们揣测我们此刻的心情,透过时空之隔,我仿佛看到史前的人们把他们象征着收获的观念制成图像,看到他们把那些象征着中的的箭镞“插”在野牛像的背上,祈祷着,诅咒着,舞蹈着,篝火映红了一张张虔诚的对“生活”充满热望的脸,这些幻象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而我的青春也在一天天地悄然生变,终于有一天,几条细小的皱纹在一夜之间爬上了我这张曾经充满稚气的脸,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游离,因深藏了明亮而变得执著而平静。
今夜一阵好雨初霁,在窗外一片青灰色的光里,在窗外断断续续的雨帘里,似传来了幽微,飘渺中蓄含着淡淡忧郁的乐音,如我的母亲站在家乡的麦田里向北方遥望的眼睛。我懂得母亲的恩情不仅在于抚养我成人,还在于老人无声注视着的温馨的目光里,在于以往每每不耐烦于老人反反复复的叮咛声里。母亲是平凡的母亲,母亲也是伟大的母亲,这无私的母爱已幻化成一种精神,镶嵌在我的意念中,融入了我的骨髓里。从落日的余晖中,从深巷中踌躇走过的老人的背影里,从我儿子的眉宇间,从我无助的企望和收获的喜悦中,母亲无处不在。我知道我已不再会因为想念母亲而在深夜独自哭泣,我知道母亲始终就在我身旁。我不再为探求艺术真谛而苦恼,我于是也知道了自己的平常,不再会因为翻阅过去而心痛,那些艰涩的日子,无疑是命运给予我的特殊的亲昵。于是也懂得珍惜情感,珍重生命中的每一天。
(1996年3月)
●弟 兄
老谢站在煌煌的灯影里,有一种久已不见的老友特有的表情。“哟,大晚上的,我说是谁呢?”这是谢的妻子从屋子里发出的声音,能听得出有一种老北京人特有的笑音。屋子里的陈设简朴,却也有条理,老谢恬然地笑着招呼大家就座,于是天南地北地闲侃,一点也不着边际,但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
约好的今天一块儿出来逛逛,公共汽车上的人很多,老谢就站在靠窗的横栏旁,有—段时间沉默,大约对方一时都找不到合适的话题。终于,你问:“家里还好吗?”答:“还那样。”你又问:“心情怎么样?”“还好。”“你呢?”谢问。“觉得有一种衰老的感觉。”“你不老,和我前年见到你时一样。”于是你们就笑。老谢还是像以前那样会说好话,让人高兴。你问:“钱赚得如何?”“总是上当,赚到一点往往一投入便亏掉了。”谢说,显得很无奈而且疲惫。
“她呢?”谢看了你一眼,说:“早出国了。”“和她丈夫一起?”“嗯。”谢答并接着说:“寄过几次照片来。”老谢的口气淡淡的,眼晴望着车窗外的远处。
美院前年新搬到了市郊,那是一个灰扑扑的地方,唯一顺眼的也只有楼下挂的那块红底黑字的红漆牌子了,你和老谢就在这儿待了一个上午。画亦然要看看的,但也仅仅是看看而已,却再也找不到先前的那种感觉。
中午的时候,和美院的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餐馆里吃饭,大家都有些矜持,这也难怪,他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封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在这儿,他们可以在冬天里打赤膊穿拖鞋,夏天里穿毛头鞋光脊梁穿皮袄。在他们看来,每个人除了自己,所有的人都是庸人、蠢货。这令你想起了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对此,你说不清自己是羡慕还是无奈,说不清自己是讥笑还是不屑,说不清是悲凉还是感慨,因为你确实有过同他们一样的感觉。
吃完午饭,我和老谢去看—个新疆的朋友,他是我在美院读书时的下三届校友,你们在一起谈了一些有关画的问题和个人的生活,恬恬淡淡地,真有点知己的感觉。
整个下午你们依旧在美院里,“现在有什么感觉?”你问谢。老谢笑一下回答说是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傍晚时,老谢说:“老沧,我该回去了,不然晚了回家又没完了,改天我再来找你。”你们便分手,看着他渐而远去的背影,你知道再见也许是很遥远的事了。
(199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