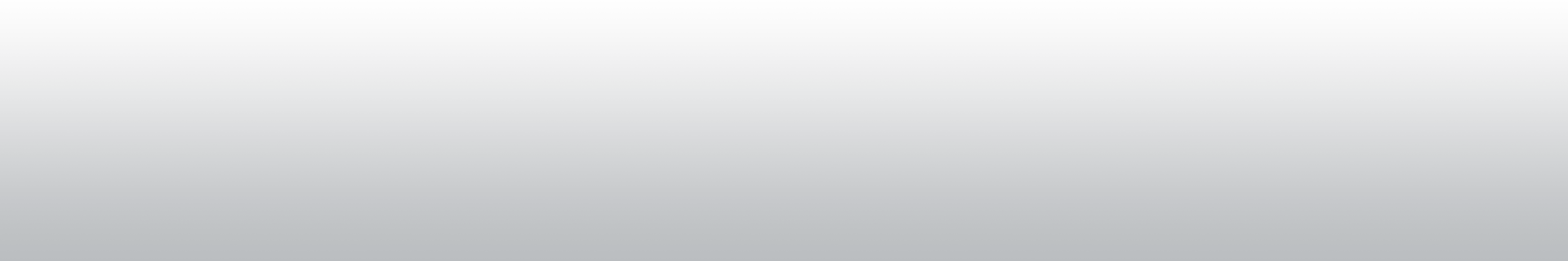从自然秩序到艺术秩序
——中国写意画的观念、法则及其对当代之影响
一、从自然秩序到艺术秩序
艺术美“是属于心灵领域”的,它缘于自然,而又和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存方式直接相关。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业文明。人们在长期的定居生活中了解自然的周期规律,认识自身之生命节奏,形成了众多与节气、时令、气候、水土有关的习俗与观念、知识与信念、迷惘与混沌、自然精灵与神异鬼怪等,并通过有关祭祀、祝祷、纪念、愉神等活动来表达,这便形成了后来文明之滥觞。中国写意绘画在后来形成发展中的认识,实际上不可能脱离这些条件导致的文化特征。从庄子的得意忘形到后来的传神写意之说,都是讲由感受到觉悟升华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 文化无疑起着重要之作用。因而中国写意画家也正是根据他所植根的文化传统通过合乎自然秩序的艺术秩序进行创作,从而突出他所处文化背景的“个性”。
以书法之笔法入画,从而完成了写意画的变描为写, 剔除刻画之弊,它标志着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绘画的另一个转型便是由重色彩转向重水墨。历经宋元诸多画家之努力,终于造就了笔涵于形、气蕴于象,诗铸其魂的高逸之风。
二、意象思维
中国画的写意性,是中国古典哲学与古典美学衍化与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孔子切磋琢磨“三月不知肉味”的执着,老子“善行无迹”的自然,庄子的“解衣般礴”的气势,以及佛家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超脱,给予绘画艺术以思想的深度,其思想内涵与审美取向构成了传统绘画的基础。因而中国写意画家并不满足于对自然物象的摹拟,而是以自然中的景物生灵为参照,借助笔墨“托物言情” ,“托物言志”。这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自然物象深刻体察之上的一种高度凝炼的情感表达。因此,中国画的写意性使人、社会、自然三者在绘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而这种物我兼容、主客体统一的创作方式,则直接来源于写意性得以生发的主要思维方法——意象思维。
庄子认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外物篇》中进一步阐释:“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易传》也有“立象尽意”之说,虽然这里的“象”主要是“卦象”,但为后来中国画艺术创作中的意象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导。王弼的《周易略例·明象》说:“夫象者,出意者也……得意而忘象。”而正是这个“得意而忘象”使中国画的创作与审美从一开始就有了写意的观念。
意象思维,是人的主观意志与自然形态的内在统一, “吾心自有造化,静而求之”。使画家在感知世界的同时反视自身,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升华,达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而作为表现对象的物象,经过作者情感与艺术禀赋的提炼,则形成了体现主体审美思想的写意性绘画形象。因而中国写意画的意象并不是执着于物象的自然属性,“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卉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画鉴》)
三、超越时空的中国写意画观念
在中国写意画表现中,并不拘泥于物象的时空表现特征,而是有画家主观情感上的超越。中国古典哲学认为, 气之聚散转化构成天地世界万物。天地间充满着无尽之矛盾,有与无、阴与阳、虚与实等等,而天地运动之和谐的原因是气,《老子·四十二章》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淮南子·本经训》说:“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具体到写意画的创作,就是画家对虚与实的认识,尤其对纸之虚白的无限生命意象的认识,简言之,纸的空白(虚无)使得笔墨及形象构成生命实现的空间。有与无的往复变化构成生命的无限发展,因此虚无的存在就不是空间的无物,虚无中有“气”之流行,“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佛家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是讲述虚无不空的思想。
所以,自然的精神不单纯局限于特定季节时令的形象,而是显示在其生生不息的生命流程中。这就要求写意绘画语言在最大限度上的纯化,而又包含无尽的意蕴。一根圆线既可以是月又可以是日,时间在这种意向之中被延续;梅花、菊花同时被展现到一幅墨花图卷中,季节的时差在这里被忽略,而四季的生命力由此得到集中表现,人的精神意向便可冲破时空的制约被集中强化为一体而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现。
四、中国画笔墨
“笔墨”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绘画语言,更是融儒道释为一体的中国写意画精神之所在。中国画笔墨语汇的精神特质和形式感给予写意画以独特的表现空间和审美取向,及至现代,由于对传统“笔墨”认识的偏离与模糊,使“笔墨”的独立价值被掩盖,否定“笔墨”,中国绘画的精神便被否定了。
五、写生、临摹与创作
写生,写物之生意也。写,倾也。在创作中对所要描绘的客观物象倾注真挚的情感,通过迁想妙得达到“传神”的境界。生,体味自然物理之生生不穷,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临摹是中国写意画传承的主要途径,以便于掌握最基本的笔墨技法、造型及构图程式。时时观摩,目识心记,久之能使法为己用。
对于已经具备创作能力的画家来说,临摹仅是对前人作品气骨风神的追思、借鉴,是在前人作品中提取与自己是艺术风格的同构因素。
写生不能滞于物,临摹不能拘于法,创作不能肆于妄。滞于物者无所见,拘于法者无所思,肆于妄者无所得。
中国写意画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合乎艺术秩序的和谐形式。自古及今,书画家在民族文化观念的基础上经过心与物之交融,代代相延,从而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笔墨审美秩序及相对规范化的形式法则,非徒描绘物象而意在写心。写物象之性灵与情感的同时,也造就了借助柔韧的毛笔、观念性的墨色、流动的水及易于渗化的宣纸为载体所建构的独特的笔墨秩序。使我们在方寸之间体现大千世界之种种意象,大到天地宇宙,小到一草一石。在特定的情感支配下,在水墨交溶之间,蕴藏着有形或无形的,已知或未知的灵性,在瞬间的灵性的感召下,化而为精神之自由,神遇而迹化,每一次挥毫都是艺术秩序与写意画家心灵秩序的重新组合。
六、构图法则
构图,习惯上又称为 “章法”、“布局”,谢赫“六法”中称其为经营位置。
构图在写意画中总是与具体的形象、笔墨、情意联系着。具体到画面上,分析其中的疏密、虚实、纵横、交叉、占角等等处理是否适当。因人而异,又赋予其个性的特征。即置阵、布势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打破原有平衡,而又求得新的平衡。
翻开国外构图学的任何一本书,总会互有异同地列举若干条一般规律,提出种种图式,如垂直形、、十字形、横向线形、斜线形、正反金字塔形、波折线形、曲线形、放射线形等,并给予一定的表现特征的定性,何者静,何者动,何者崇高,何者安定之类,构图规范的依据是人们在生活中得来的视觉经验以及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的审美经验,虽然东西绘画从审美观念到工具材质各不相同,但中西方绘画构图,在视觉心理规律上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
事实上历代写意画所谓的“有法与无法”都是写意画家心灵自由与艺术创作纯化的表现。石涛云:“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旨也。”所谓“不舍一法”是指对传统的借鉴、继承;“不立一法”则是指不囿于成法,不执著于一己之法,法随机异,方能生生不穷。“不识本心,学法无益。”“有法”、“无法”只是在特定时空下对待创作的一种态度,如果能回归古典精神,复归于朴,那么,就不会囿于“有法”或“无法”的执著。
七、观念的色彩
在我国的写意绘画中,历来讲究以水墨为格,唐代张彦远有“运墨而五色具”之说。唐以后水墨似乎比色彩更被重视,中国画最突出的特征是笔墨,追求色彩势必弱化笔墨,在绘画渐而趋向写意之漫长的演化进程中,道释理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引申于画,便是其“取法其质,独尚水墨”。这无疑显示了中国画写意的特殊性,尤以有宋以后,儒道佛之互为参证,从而形成的中国文人特有的水墨写意之观念。写意绘画,实则是“画中设色所以补笔墨之不足,显笔墨之妙处。”
同时中华民族特有的包容观念,又善于把外来的文化观念融化在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利玛窦到郎世宁,从扬州八家,以至于虚谷、赵之谦、任伯年等海上诸家,乃至于近现代之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在他们的绘画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外来的在作品中被本民族文化观念融化与消解的轨迹。
对自然的亲近,对大朴无华的心灵体验正是中国写意画家共同的特点。中国写意画尚淡、尚静、尚纯,亦如阿恩海姆所谓:“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禅宗讲:“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一点一画,隐迹立形,备遗不俗,如此清华之笔墨,皆在于发诸心意,是其在特定的环境下精神的一种放逸方式。
九、禅宗写意
唐宋间,画僧文化修养颇高。僧人与文人画家交往者众;加之其间文人多儒表佛里,如唐之王维,宋之苏轼等莫不于佛教禅宗思想多有沾概。宋初僧石恪以画僧佛见长,虽时见缺落,却不掩其美。及至南宋景泰间画院待诏梁楷、僧法常、玉涧诸人,皆善水墨,作禅意绘画,为后世之楷模;入元后又有方方壶,元四家推波助澜;明末清初僧人八大、石涛、担当及黄山四僧等,众家纷呈,禅宗写意之风呈一时之大观。明代画家沈周极为推崇法常的作品,他的写意花卉蔬果画风显然受到法常的影响。由此可见,禅宗写意画也的确影响了写意画的发展。
“人须先变成神圣的和美的,才能观照神和美。”写意画实也应如此。作者先“顿悟”,“明心见性”,才能观照自然之内在精神。
黄檗断际禅师尝云:“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禅宗“一”与“无形”的体现是直接的、自由的、无挂碍的。写意画家不为表达众多而体现众多,不为体现众形而描绘众形,众多即“一”,“一”即众多,而有形是用来表现无形的精神。
十、回归和谐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中国绘画与自然内在相通,“艺者,道之形也。”(清•刘熙载)大自然春温和秋肃,都是和谐,惠风和畅与飘风顿起都是和谐,波平如镜和狂澜排空都是和谐。美的和谐便是与道相通的中国绘画的境界。
作为艺术家要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其忧患意识应推及对地球、人类整体生存之终极命运的深切关怀。如何使人类的小智慧去顺应宇宙的大智慧,这是当下及以后所应深自反思的问题。现实情况下,对地球、人类的终极关怀还要借助人文关怀,借助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和”,儒家的仁恕、中庸,佛家的寂静、涅槃,道家的返璞归真,所有这些东方哲学或宗教对理想境界的追求都是和谐的、圆融的、静穆的。东方文明有着空明、博大、典雅、雄浑的特性,而中国的诗、书、画则把追求平和、雍容、温柔、敦厚作为极则。
现当代的人文主义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已有了完全不同的内涵,那时人文主义的对象是神学和经院哲学。而今天的这种充满矛盾的时代背景下,人文主义的内容只能是对地球和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地球有大气、有水分、有生殖繁衍的条件,如果这些受到破坏,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因此,尽管艺术家本身做的都是很微小的事情。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能唤来一种全球的力量。
仅仅依赖科学技术的物质力量不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艺术的力量看似乎微末,但其塑造完善人格、净化人类心灵的潜在力量确实是巨大而长远的。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艺术,蕴涵着人文精神,其在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当有不可替代之用。我们应该从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寻找那生生不息的活力,增强自身的造血机能,使古老的文明发出新世纪的光辉。重新将古典主义赋予新的精神内涵,从而使艺术在新的高度上重新回到它的本原。我们将充分肯定和珍视宇宙的自然之美,因为正是它们唤起人们趋向真、朴的境界,这才是人类艺术的方向,中国写意画的精神即是这种与自然和谐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