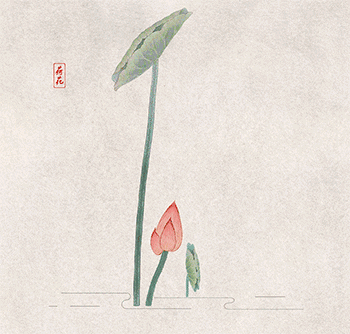


尹沧海
自然之美在艺术上无法用科学性的理性的逻辑推理来获得,自然有“大美而不言”,在中国哲人心中宇宙自然是混沌而又有秩序的存在,混沌是“道”的无差别的形而上存在,秩序是“器”的有差别的形而下存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自然事物有“一”“二”“三”等秩序的差别,秩序的差别最终要回归到“道”的存在方式,而“道”是混沌的存在,所以,秩序的差别要归于“和”,归于和谐的存在。自然界各种事物之性质的差别导致一切具体事物相反又相成、对立而又统一,由此使自然界达到某种和谐的秩序存在。如果一味强调自然事物之间的分别性,就会导致矛盾的激化,从而混沌与和谐秩序便会消亡。所以,万事万物“五色”“五音”的丰富差别要回归到混沌的“道”。由差别的对立性带来的斗争与无序是暂时的,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即是矛盾激化的斗争状态的暂时性,最终还要回归于“和”的秩序。
人类的知识相对于广漠的宇宙自然,仍然非常有限,我们仅仅揭开了大自然的一个角落。艺术家观察、描述自然的内动力,不仅仅是对自然神秘莫测的力量充满惊异和对自然和谐秩序之美的感动之情,艺术家的敏感被触动同时还来自悲悯而良善的人类天性。正如范曾先生所说的:“每当我登高临远,仰视天宇之大,俯察品类之繁,我常常产生一种对万物生灵的无限恻隐之心。也许只有我陶醉于这种远离尘嚣,宠辱两忘的境界之时,我更接近了大自然的真、善、美的本性。”艺术家对自然的体察,是“以诗人之眼观物”,则眼中之物,亦非自然之物,“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更是寄托了创作者的情感。因此,一个艺术家的胸次学养,天性人品,就决定了他对自然之大美进行观照时体悟的深浅。就中国画创作而言,创作前的理性认识过程又往往会成为创作过程中的某种障碍,在这种障碍之下,诉诸笔墨的画面有时仅余下了我们所要刻画的物象之表象秩序。那些真正令我们感动的、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来的精神却又稍纵即逝,而对于这种稍纵即逝的精神的把握,往往是反映在创作之中高度自觉的、能动的即时发挥,在这里心灵在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里表达出了个人的气质与理性之沉淀以及自由与意志,而人的心灵也同时在领略创作过程的同时得以丰富。范曾先生曾剖析这种由“器”而入“道”的抽象过程,即“远离物象,走向形上”。
“破障”的过程,即是庄子所谓的“坐忘”。借孔子之口,庄周说过:“……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也者,心斋也。”又“……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心斋”“吾丧我”的意境便是坐忘,而坐忘意在消除个体之知,是美的自觉的活动,坐忘乃为有知而忘知,忘知的根底还是某种程度的有知与知识,不然,知觉特性则无以发挥,不能上升到美的自觉的高度。坐忘的历程就是对美的观照的历程,是书画艺术(尤其是中国画写意)的写生与创作过程得以成立的主要依据。
达到心斋与坐忘的历程,一是消解世俗之欲念,使心无役于物,精神方得以自由。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以美的态度观之于物,则心境愈自由,便愈能得到美之享受。”二是心与物相接时,心并不对物做知识性活动,从而免除知识活动带来的是非判断,心灵摆脱烦忧,从对知识的追逐中得到解放。凸显出物我之间的主体感悟,即美之观照。用一丛花作比,在创作过程中,你在感知它的和谐与美感的同时,并不以理性之概念来解析它,因为如此的注释永远与处在审美状态之中的创作过程不相干,在美的观照下描绘,才能得到离形去知之境界,而这种境界的获得,并不脱离自然之花的本性。此历程非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而是一种纯感悟活动。在这样的创作状态下所传达的艺术精神,虽然是一己的个性表现,却更能够直达物象本质,因而,也就体现了自然之秩序,并表达了艺术秩序。这在佛家谓“梵我如一”,在道家谓“体道合一”。对于这种创作状态,史料上亦常有记载。如庄子的“解衣般礴”,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已成书画家之口头禅,书画家必须心有主宰,胸储造化,手具熟练技巧方能“遗去机巧,意冥玄化”,得心应手。一个画家,他们敏锐的感觉是在千万次的实践,千万次的心、眼、手配合锻炼的前提下,逐步得到的。这种创作状态可以称之为美的观照。
书画家对自然之理论与知识的掌握,对绘画过程来讲是必要的,比如画一幅以花卉为题材的写意画,了解花叶的向背、花朵的生长规律、枝干交叉的秩序,有了这些理论的认识当然不等于我们就能画好一幅画,重要的在于我们在作画时的状态,也即坐忘与离形去知的过程,然后才有觉悟的生发。这个过程当然需要在创作中去体验,离开了具体的创作体验来谈书画创作的坐忘、离形去知之类,便会堕入玄谈。
有时,当我们从梦境中醒来,或不经意地看见窗外的阳光隔着窗纱,斜射进来的光柱中飘舞的微尘,或者墙壁上的光斑及裂纹,有时自然会联想起诸多类似物像的图形。在想象力的驱使下,图像会凭空凸凹并活现在我们的面前,想象力会为眼前的图像进行主观增减,这一切都是这么简单而又神奇。一些西方绘画大师们的手稿,尤以他们的一些类似速写的小稿,往往比较清楚地告诉我们艺术家是如何以他敏锐的感觉对待人们看似平凡的事物,并由此而发掘出人们潜意识中共通的东西。明代画家王履说:“对景造物,难以造微,然而却能摒去旧习,以意匠就天出侧之。而有天出之妙,或不为诸家畦径所束。”
事实上,中国书画家(尤其是写意画家)重写心,重情感,重心与物的交流,重观念的神采。在特定的创作情态下,看似几根简练的线条组合却有着独立的审美寓意。面对一丛鲜花,若要将它描述出来并不费力,但如果凭瞬间的感觉捕捉到蕴藏在花朵里的内涵,将人们心里不可言说的感觉通过画面表现出来,成为人们所赞叹或共赏的艺术作品,这便需要有常人所无法企及的感知觉。由于中国书画的特殊性,一幅好的书画作品的诞生,往往与一己之审美经验有着紧密联系,而最终能否经得起检验的依据,则是它能否与众人共享或者说引起共鸣,即在相同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影响下能够做出特定审美判断的人群的共鸣,对艺术家本人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品位的评价,是通过对作品本身的欣赏而得到认同。我们不能否认,即使是一个平常的人,也都有基本的艺术感知能力,这便是天地大德赋予人类的审美基因。

